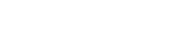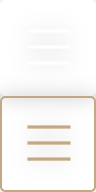东横河:父亲的河流
——我家的苦乐园
徐梅强

作者徐梅强 李斌摄
翠屏山脉北边,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河流,它西接姚江,是浙东运河的一条支流。这条河叫东横河。
我出生在东横河北岸一个叫做新桥头的村庄。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现在住的那个偏僻民居,是在乡间过去叫做“涂山”的地方。那里位于东横河南岸,与我小时候的故居老宅只有一河之隔。涂山是一座大约高六七十米,孤独地耸立于田畴中的小山。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包括很多祖先都安葬在这座山上。小时候爬过多少次,实在难以数清。年轻时在山前山后的土地上劳作,总是期盼自己何时能脱离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后来,我如愿去了城里。后来,这座挡在我们村前的小山被“愚公们”采石挖平了。爷爷和父亲的坟墓迁到了另一座公墓山上,而这里建成了一处住宅小区。三年多前,我鬼使神差地竟看中了这里的一栋房子,来了个彻底的“回归”,舍弃了越来越熙攘的县城,把家安在了这里。
涂山没有了,但涂山和东横河不可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那架快要老掉牙的“思维机器”,咔咔响了几下,终于转动起来,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我的八十年前的爷爷……

东横河上七星桥资料照片
我的爷爷
他的这一趟回家的行程,走得异常的艰苦。两年前,盼望了多年的钱塘江大桥终于通车了,本以为过年回家的路会顺畅一些。但哪里想到,老乡蒋总统集中了那么多的中国军队,拼死拼活跟日本人打了三个月,淞沪会战还是失败了。刚通车一个月的钱塘江大桥,被国军自己炸断,还把萧山到曹娥江刚造好的鉄路轨道全扒了。屈指算来,在十里洋场的日子,混得也算有年头了。从刚来时做些小生意,到后来开办商铺,从商铺又转成公司。眼看着买卖越做越大,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打下了上海滩。他与朋友把合办的商贸公司搬进了公共租界,生意是难做了,也不至于回家种田吧?在上海滩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不说再也吃不了这个苦,更丢不了这个面子。
但这一次,他已打定主意再不回上海了。上海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民国后宁波人在上海商界建立的统治地位失去了,一切都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公共租界也朝不保夕,还是趁早走吧。前些日子,他把在上海的所有财产全变卖了。唯独把这些年在上海陆续收买的数百幅字画整理了一遍,随同衣物和一些古董,装满了十来个大小箱子。租了一辆车,把自己积累了半辈子的财产,直接运到了杭州钱塘江边的码头上。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桥早断了,路也不通了。在码头的客栈里待了几天,他终于等到了一只去曹娥江的快船。接着又顾了一只脚划乌篷船向家中赶去。从杭州到余姚东橫河边的老家,整整走了八九天,日本人、国军、忠义救国军加上土匪地痞,也不知过了多少关卡,数不清花了多少银子,但他终于回家了。
爷爷走上东横河北岸自己家的船埠头,邻居家人纷纷赶来迎接,唯独不见我当年十二岁的父亲。有人说,父亲背着铁耙,带着篮子好像到涂山挖什么去了。刚说完,几个比父亲年长数岁的捣蛋鬼,憋不住哈哈大笑逃走了,一边说范少爷到山上挖蛤蜊去了。一会后,父亲一身烂泥,垂头丧气提着空篮子回来了。这个故事,在我的少年时期,老辈人以嘲笑的口气,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过数次。父亲从小生长在农村,但由于家境优裕,从来没有吃过苦。那天是几个调皮的伙伴,合伙捉弄他。当然,涂山之所以叫“涂山”,过去肯定是滩涂边上的山,也肯定生长过蛤蜊。青少年时代,我也见过山上许多白色的贝壳,但那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事了。当然,我不会去挖蛤蜊,小伙伴们骗不了我。我不是“少爷”,我是个苦得不能再苦的苦孩子。
爷爷长得挺拔,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在村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已近百岁、从小跟着爷爷在上海念书的姑妈说,爷爷在上海做商贸生意,还与人合开了一家博彩公司,但他自己从不参与。逢年过节回家,一见到乡里乡亲在赌博,他会一把抓起赌具扔了,还骂一句:匹贼,不好好做人,也想学赌?这会害死人的!爷爷见多识广,乡里人只好认他的骂。
我的祖宅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大房子,附近乡邻称作“大墙门头”或“七房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祖宅临东横河而建,应该是在太爷爷时代置办的家产。老辈人传下来说:太爷爷是个成功的商人,挣了不少钱。造这“大墙门”大宅时,直接从姚江顺着东横河撑了一长串木排过来。爷爷排行老三,兄弟四个。大爷爷成家育女出嫁,但无子嗣,小爷爷没有成家当然无后代。二爷爷十几岁就考中秀才,至今留下少量墨迹,一手漂亮的小楷,看上去就像木版印刷一样娟秀工整。大爷爷去世后,我爷爷接收了大爷爷的家产,合并成了大墙门内东边的一半;二爷爷接收了小爷爷的家产,合并成了大墙门内西边的一半。每到清明时节,我都会到爷爷的坟头烧烧纸钱,点上香烟〔爷爷生前抽烟,专抽铁盒装的“哈德门”〕,磕头祭拜。当然,二爷爷家的子孙、玄孙多得去了,不缺烧香祭拜的后代。如果真是“地下有灵”,那大爷爷、小爷爷的“灵魂”要痛苦得多。因为无子孙给他们烧钱祭拜,也不知道他们埋骨何处。据我理解,我们当地流传的所谓“香火”,就是每年清明前后有子孙去坟上添土烧香,再在家里买些酒菜“做祭日”烧烧佛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原来就是为了此。但不管怎么说,有子嗣后代还挂念着祖宗辞去的亡灵,肯定是件好事。
回家后,爷爷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忙着把上海大小姐般的姑妈,嫁给了东横河南岸“大屋里”一个家境一般的农民。前些年老姑妈说起,还耿耿于怀。日本人来了,谁都不敢把大姑娘留在家里。东横河上的桥梁几乎都扒了,桥南是国共的游击区,桥北则是日伪军的天下。爷爷在地方上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两边都不得罪。厅堂里不时更换着从上海带回来的字画,找几个好友鉴赏一番,日子过得清闲,但也时常心惊肉跳,除了应付日伪和“上山”的人,晚上还要提防如毛的盗贼。有空的时候,爷爷会渡过河,到“大屋里”姑妈家坐坐,顺手带几把女婿在地里种的新鲜蔬菜。大屋里向南隔着大半里路田畈,就到了涂山脚下。大屋里的旧址,是一座天官府的深宅大院,传说当时这座宅院里有十八口水井,可以想象当年的院子该有多大。隔着东横河,河的北岸同样是一座规模极其宏大的布政使家大宅。现在手机的百度地图上,还能搜到“荷花池”这个地名,荷花池的北面,有一处东西走向长约半里地叫“假山”的高地。这东横河南北两处大宅,其废墟规模不小于苏州那些著名园林。但这一切的一切,在1860年前后被“长毛”(当地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俗称)几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长毛在烧毁我们这一带宅院同时,进行了血腥屠村。160年的历史并不长,我从小到大,从没有从老辈人口中听说过,谁谁家是大屋里或荷花池大宅院里传下来的子孙。
我的祖宅“大墙门头”,应该是长毛造反后这一带重建民居中最好的宅院之一。爷爷回家后好景不长,不久就感觉到身体不适,以后就生了一场重病。为了治病,花完了从上海带回家的所有积蓄。积蓄花完了,就卖古董和金银用来治病和度日,但他从来不舍得卖多年积攒下来的字画。两年后,除了留下大墙门内的半边宅院和传给子孙的数百幅字画,就撒手人寰离世了。爷爷死后还吃尽苦头。爷爷在附近名声太大,盗贼们总以为爷爷是有钱人,总有金银珠宝陪葬。趁着月黑风高的夜晚,几次撬开了他下葬的棺木……
那一年,父亲虚岁十四岁。那一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处于战乱,但不远处的翠屏山脉依然青山如黛。东横河虽断了桥梁,河中如梭的船舶还在往来,岸上纤夫的脚步依然如织。河水依然清澈见底,河岸上依然还是一派田园风光。
我的父亲(之一)

淮安漕运博物馆 桑金伟摄
父亲生于1928年,他身躯挺拔,好像从来没有弯过一次腰。2005年去世时,他的身板还是直得像一名老军人。父亲始终绷着脸,似乎没见过他有笑容满面的时候。只有一次是例外:1999年7月那一天,他一早来到我的工厂,得知我爱人生的是儿子后,他失态地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禁不住哈哈大笑了好几分钟。我至今还是不明白:父亲当初也应该知道,他很少有可能吃到孙子的“食”,但他为何如此兴奋呢?他这一辈子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从不跪拜菩萨甚至祖宗,难道他图的,也是孙子未来能在他坟头点上一烛“香火”?
爷爷去世后,父亲的少爷好日子也到头了。父亲十七岁时,还懵里懵懂的,娶了邻村比他大两岁的母亲,母亲的父亲是做油漆匠的。我不敢亵渎我已经过世的双亲,但我还是要说,不知道是谁做的媒,因为这注定是一桩难以美满的婚姻。家道中落的父亲,还是改不了少爷的臭脾气,稍有委屈,就会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个子娇小的母亲身上。父母婚后虽有争吵,日子还得过下去。第二年,我的哥哥出生了。家里虽然还有几亩田地,从小娇生惯养的父亲,怎么也习惯不了在土里刨食吃的活法。无奈之下,他走上了爷爷走过的道路:离开东横河边的宅院,舍妻弃子,去远方的城市讨生活。父亲没有去爷爷曾经闯荡数十年的上海,而是去了西湖边的杭州,开始了“学生意”的日子。
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到过:1949年5月一天的傍晚,远处不时传来轰隆作响的炮声,杭州城里的店铺都关上了排门。国民党所有机构和守军,杂乱中匆匆作最后的撤退。钱塘江大桥修复刚好一年,国军工兵第二次装满炸药准备炸桥,企图阻止势不可挡的共军南进。第二天清晨,父亲从店铺排门的门缝里发现,街道上站满了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一身尘土,甚至衣衫褴褛。父亲听见一名老家口音的军人,在敲旁边的店铺的门,好像要买什么东西。后来,那名军人的手指头,敲在了父亲所在店铺的门上。父亲忐忑中开了门,那位军人想找墨水,刚一开口,两人一下子都愣住了:这位军人是父亲的少年同窗,后加入三五支队,北撤三年半后浴火重生,重新打了回来。
解放了,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奶奶多次托人,要父亲回家参加土改,因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土地。父亲犹豫着从西湖边的杭州,回到了东横河边生他养他的宅院。为了一份土地,他尝试着耕耘和收获,尝试着做一个“务农财主万万年”的真正农民。但父亲怎么也忍受不了做一个农民的艰辛和寂寞,有一天,他终于爆发了。那天,父亲正在东横河边用手摇水车往稻田里车水,由于没有耕牛,他只能用这种低效的笨办法灌溉稻田。盛夏时节,酷热难挡,父亲汗流浃背。这时,缠着小脚的奶奶,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提着水壶,艰难地走过大墙门东边东横河上的石桥,小心翼翼向正在跰手阺足劳作的父亲走去。父亲没有吃奶奶担来的点心,接过水壶猛喝了几口。但奶奶担来的茶水不但没有浇灭父亲心头的郁闷,反而使他的一腔怒火升腾起来。父亲一甩手,把茶壶扔进了东横河,对着奶奶跳将起来:种田、种田,种个屁田!说罢丢下水车,扬长而去。
父亲再不想种田了,他也没有什么鸿鹄之志,虽然他体魄健壮,但他受不了做农民的苦和累。杭州是回不去了,但生活还得过下去。父亲苦闷了一些日子,终于等到了机会。解放后百废待兴,各地兴办学校,普及小学教育。父亲充其量只有小学毕业水平,但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他被分配到当时靠近海塘边的胜北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此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父亲生前曾美滋滋说:每到秋风乍起,学校的河塘边,甚至棉地里,会爬满一只只又肥又大的螃蟹。一早起来他们就去捉,锅里一煮,那肥美的螃蟹,味道真是好极了……在那填不饱肚子的岁月里,我听了每每垂涎欲滴。父亲少年时没有挖到涂山上的蛤蜊,但成年后却吃到了海塘边肥美的大毛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美事。而且喜事连连,他不但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国家干部,而且还成了解放后全县教育系统第一批入党的中共党员。
父亲春风得意了几年,但接下来是他倒霉的日子。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党畅开言路,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向政府提建议和意见。积极要求上进的父亲,加入了这一运动。也许是“建议和意见”提过了头,没多久全国风向突变,积极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成了《聊斋》中终于跳出来的“牛鬼蛇神”。整风反右工作组开进了父亲所在的乡镇,父亲当年的同事后来对我说,你父亲当时不是内定的“右派”,人家的“错误”比你爹严重得多。“人家”一看风向不对,马上向工作组痛哭流涕承认“错误”下跪了。“人家”只要不被戴上“帽子”,可以自己打自己的巴掌,也可以骂自己的祖宗十八代。但你爹性格太倔,死不承认自己所提的建议是错误的,不肯写检查,生生地把别人的右派“帽子”,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我出生后不到两岁,父亲被开除党籍,和县里的一帮“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龙山水稻农场,接受无期限的劳动改造,父亲不想做农民,但他还是被迫做了不是农民的农民。父亲可以扔掉奶奶递给他的水壶,但他扔不掉自己头上“右派”这顶“帽子”。由于“改造”积极,一年多后,父亲终于摘掉了头上的这顶“帽子”。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即使你“摘了帽”,那顶无形的“帽子”会永远地套在你的头颅上,甚至连带着把你子女的手脚一起绑上。
紧接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全国55万爱说“闲话”、敢提“意见”的牛鬼蛇神被关进农场牛棚,让他们闭了嘴。于是,“公社是朵向阳花,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的优美歌声,在每个村庄的高音喇叭中唱响。全国每天都在热火朝天地“放卫星”,“千斤棉花万斤稻”的时代来临了。家家户户粮食被收交,放到大队里的大食堂,你自己连饭都不用做,就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这是一个多好的年代啊,忽如一夜春风来,似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但、但……这个“但”字实在太过沉重,饱饭没吃上几天,经年累月饿肚皮的日子到来了。我属猴,那时更像一只小小的瘦猴。奶奶整日怜悯地抹着眼泪念叨:这个小孩,总要饿死的……这个小孩,总要饿死的……
我终于没有成为饿死鬼,这要感谢我那伟大的母亲,当时忍辱负重的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为了不被人家瞪白眼,她拼死拼活,日以继夜地在生产队的田地里忙碌着。东横河两岸的土地上,留下了母亲瘦小的躯体里流出来的鲜血和屈辱的眼泪。母亲整日在饥饿中劳作,为了不让我饿死,她从牙缝中省下的一口饭(这个用词不确切,当年不可能有饭吃,应该是一口粥),给我这个小儿子吃。
两年多人间地狱般的食堂时期结束了。几乎在同一时期,父亲在龙山水稻农场的“劳动改造”也告了一个段落,他被重新分配到一所中学,担任了学校的后勤总务。也许这一时期各地饿死的人太多, 1960年下半年,全国又掀起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高潮。父亲内心世界是个“粗线条”的人,但他不管有多粗心,总不能看着一群饿得面黄肌瘦的儿女嗷嗷待哺吧?父亲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再说自己这个“摘帽右派”在学校里也难以过得顺心。当年父亲是因为没有写“检查”而蒙受灾难的,这次却下狠心主动打了报告,要求回家去“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做一个真正的农民。
父亲回家了,但他这辈子注定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不是说做就能做成的。有朋友聊起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做了多少年的农民,我从来不予认同。也许是遗传的原因,我的性格耿直得与爷爷、父亲如出一辙,我说,假的,农民有这么好做的吗?最多你在农村混了几年日子。如果不是出生在农村,从小在土地上摸爬滚打,你在农村待一辈子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文学界的几个朋友,凑到一起,总喜欢打那种叫“拖拉机”的扑克牌。一段时间,我与一位好友一起打牌,不管手中扑克牌四色花中的“草花”牌最多,他也从不叫“草花”为“主”。他说我是农民,我手中的“草花牌”肯定最多。我说我早不做农民了,我从小做农民,在土地上耕耘了十几年,但这辈子我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再说,我们这里的农村,现在还能叫农村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东横河两岸的农村还是真正的农村。父亲回家后,这次想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他一头扎进家乡的土地里,但家乡的土地已经不认他了。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把我的祖宅“大墙门里”房屋的分布,粗略地描述一下。否则,我以后的故事就很难讲清楚。现在看起来,祖宅也不能算是一个很大的宅院,它只是一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而已。祖宅朝南对着东横河有五间高大的正房,中间一间特别宽,叫堂前间。堂前间有前庭,前庭后是一道六扇门组成的堂前门,进门就是宽敞的中堂。中堂北侧有一道门,叫“簿子”门。簿子门上方有一整排叫“神堂”的阁楼,上面摆放着祖宗的牌位。堂前间东侧是我家的两间正房,正房有地板,还有油漆很厚的阁楼。正房前面是一个小天井,一东一西摆放着不知从哪个年代留下来的两只大水缸。小天井的南边,对着庭院,是我家另外三间朝西的侧屋。侧屋有甬道,通向北面的正房。
我父亲回来的那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无风,天气闷热得难以入睡。住在堂前间西侧正房的堂兄大哥〔其实堂兄大哥比父亲还大两岁〕,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刚睡着,但被堂前间中的拍门声惊醒了。起来一看,门关得好好的,半夜三更哪有人呢?刚睡下,拍门声又“啪啪”响了起来。反复数次,堂兄终于听到了东房父亲“哇哇”的呕吐声。那晚母亲刚好不在,堂兄撬门进去,见父亲痛苦地喘着粗气,已经快不行了。堂兄叫起了大墙门里的本家男人,把父亲送到了医院。父亲白天在棉田里喷洒农药,到了晚上药性发作,差点要了他的命。
此后,乡邻们啧啧赞叹:我们七房里头的祖宗,太有“灵性”了。但祖宗真有灵性,也难保佑父亲做一个真正的农民。不久,大队里办了一家轧米厂,当时谁也不会操弄机器。父亲总算有点文化,就让父亲去了轧米厂。此后,父亲除做过几年抽水机手外,就一直在轧米厂挣工分。他常年一身柴油味,记得小时候,父亲顺手会给我洗一把脸,我不好拒绝,但毛巾上的柴油味,至今一想起还忍不住想吐。
我的童年和少年
 淮安下河古镇。桑金伟摄
淮安下河古镇。桑金伟摄
我不能在饭前想我的童年,我一想马上就会觉得肚子很饿。六十年了,依然如此,条件反射,恐怕这辈子难以改变。以至于出差、国内外旅行在酒店用自助早餐时,稍不留神,就会拿一大盘子食物,随后不得不硬撑下去,搞得自己十分狼狈和尴尬。
但少年时代的记忆,在我心中要美好得多。每当莺飞草长的季节到来,我的眼前是一片片金黄色的油菜花,一阵阵温馨的东南风吹来,碧绿的麦田像一片片波涛在微风中荡漾。放学归来的我们,人人背一只竹筐或“牛草蓝”,去田野上割一筐野草。那时,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养一头猪和几只兔子,在家中,割草喂猪喂兔子是我们这些孩子的职责。我们一般先会在田野上玩耍,躲进油菜地、麦地里捉迷藏。或者趁生产队的大人们不在山下干活,溜到涂山上,偷偷摘几把黄豆般大小的杨梅放在裤袋里,随后跑到山下,身子一歪躺在尺把高的、开满了紫色花朵的紫云英田中,一边咀嚼着酸酸的小杨梅,一边闻着繁花和泥土的芳香。碧蓝的天空中,去南方避冬的燕子回来了,在头顶飞来又飞去地欢叫……
夜晚,我肦望着春雷隆隆震响。一打雷,春雨就哗啦啦下来了,我侧耳听着,就像在欣赏一段美妙无比的音乐。第二天清晨,天还刚蒙蒙亮,我拿起鱼网就蹑手蹑脚出了家门。东横河南岸的大水沟里,一群群逆水而上去产卵的鲫鱼们,实在是太肥美了。手掌般大小的鲫鱼在网兜中翻滚跳跃,拼命想从你的手中挣脱出去,那种感觉十分刺激而又十分幸福。
最好玩的季节是在夏天。那时,我们大队是县里出了名的“绿化村”。东横河两岸我们村庄的每个角落,每家每户都种碎叶子、开紫色小花的苦楝树,整个村庄掩映在苦楝树的一片浓荫之中。盛夏的中午,知了爬在苦楝树的枝条上声嘶力竭地叫喊。夏天谁都不穿鞋子,我们拿一根长长的粘知了的竹竿,光着膀子在斑驳的树影下从村东晃荡着走到村西。或者用稻草搓一截绳子,套住两脚,爬到树杈上睡觉。
最兴奋的时间是在下午放学后,我们常常为先去割草还是先去游泳而拿不定主意。一百多年前,长毛烧掉了河两岸的深宅大院,给我们村里小孩子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后来倾倒在河道中的一片瓦砾滩。它使我们祖宅故居前面的一段河道,成了天然泳池。顺着东横河往东走,不出五里路就到了上林湖。那时的上林湖水,主要是为了灌溉农田。夏天少雨,一到下午,上林湖就开闸放水。河道上缓缓向西流动的湖水,清澈得能看清水中流鱼和河底的瓦砾。河滩东边的石桥下,由于桥洞狭窄,水流就很湍急了。
我们每天傍晚就在这清亮的水中游戏玩耍,常常把手指头泡得像“麻皮豆”。当时东横河上有两种主要运输船只,一种是方方正正、颜色漆成红色的“红头百官船”,另一种是船身很扁很浅的“奉化缸甏船”。这两种船只属于正规运输公司,往往前面是机船,后面拖着五六只同样大小的船只。上林湖放水时,逆流而上的一长串船只,往往要开足马力,才能通过水流湍急的桥洞。红头百官船吃水深,很容易搁浅。红头百官船的船老大们,最恨我们这帮常常捉弄他们的“小鬼头”。我们学电影中的小兵张嘎,大老远看见船队过来,就潜入水中搬大石头,一块一块垒在了桥洞口,随后就逃开躲在一边看热闹。机船“啪啪啪”冒着黑烟开足马力向桥洞口冲去,却轰隆一下被水下的石堆卡住搁了浅。拖在后边的船只,顺着巨大的惯性向前冲,船佬大们急了,赶紧拿起撑篙跳到船头,死命地把船顶住。一瞬间,整个船队乱七八糟横在河面上。我们跳上河岸哈哈大笑逃走了,船老大跺着脚骂:啊,这帮小爹爹,看我不打死你们!
这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大概在八至十三岁的小学时期。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公社和大队里的红卫兵,除了揪斗走资派,还每天敲锣打鼓地“破四旧、立四新”,吓得本来就胆心又想“进步”的哥哥如惊弓之鸟。有一天他终于熬不住,把家里藏有爷爷从上海带来的字画一事供了出来。红卫兵头头有点怕我父亲,就让我哥自己去处理“四旧”。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哥和我的一个堂哥,用一个箩筐,把爷爷费心从上海带来的一卷卷字画,连同一些古籍和家谱,一筐筐从阁楼上吊下来,然后堆在了堂前的庭院里。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架起梯子,打开多年尘封的神堂门,壮着胆把一个个“木祖牌”〔祖宗牌位〕拿下来,一起堆在撕得粉碎的字画上,接着点了一把火。熊熊烈焰升腾了起来,蹿得老高老高,突然“呯”地一声巨响,火堆下的一块石板爆裂了,有人心有余悸地喊道:祖宗显灵了,祖宗显灵了……
唉,祖宗再也不会显灵了。这场革命,把祖宗的“命”都革掉了。
没过多少日子,我那无忧无虑的岁月也跟着结束了。
1970年夏天,我虚岁十五,足岁十四。不知不觉中,我读了两年的初中,一眨眼就毕业了。那时的农村,无论大人孩子,谁都不会把读书当回事。但临初中毕业,我却突然刻骨铭心想要继续读书了。结果大失所望,大队上高中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天好似一下子塌了,我感觉到,如果上不了高中,今后的世界就没有我的一块天地。我大着胆子责问当大队书记的堂二哥:我成绩比那位推荐上高中的同学要好许多,为什么不让我读高中?堂二哥比父亲只小了一岁,支支吾吾了好一会,我马上明白过来。中午父亲回家了,我豁了出去,准备再挨一顿父亲的拳打脚踢,我泪流满面冲到父亲跟前,两眼怒视着父亲大声咆哮:爹,你过去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犯了什么罪?!
父亲高举着的大巴掌颓然软了下来,大嘴开合了好一会,最后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我心里恶作剧地想:你解放前为什么不去入共产党?要是被国民党抓了,肯定能做烈士。即使你死了,我们现在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这时我突然发现:从来天地不怕,鬼神不信的父亲,两眼竟然噙满了泪水。
我突然愣住,我似乎一下子明白,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从那天起,我几乎没有了欢笑,我一天不歇地在生产队里出工、收工,我咬咬牙认了命。哥独立分家出去了,他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年底到了,我想看看一年中有什么收成。大开本的生产队年终结算方案表上,我找到了父亲的名字,我两眼一下子直了:“倒挂”180多元?全生产队七八十户,我家竟是“倒挂”最多的一户!从此后,我想继续上学的心彻底死了,我是男人,我要分担家里的责任。我暗暗下决心,争取三到四年,把欠生产队的“倒挂”还清!
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五岁时我家的那个年是怎么过的。倒挂意味着一家人在生产队干了一年活,分配了粮食、柴草后,不但在队里拿不到一分钱,还欠了队里其他人的钱〔后来,我在生产队当过好几年会计。生产队的核算、分配,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过了大年廿三送灶的日子,家里一共才凑了五毛几分钱,父母商量着先做半锅豆腐吧〔一锅豆腐需一元钱加工费〕。但光吃豆腐和豆腐渣还是难过年,父亲心一狠说:把猪杀了吧!那头光吃草糠的黑猪,才六七十斤重,宰了实在也是可怜。
两家邻居出于同情,一共给我们买了五元钱的猪肉。1971年春节,半锅豆腐五元钱,一家五口,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我的母亲
母亲去世已二十五年了。去世头几年,我不能提到母亲,因为一提起,鼻根发酸,接着眼泪就会止不住地流出来。母亲这一辈子,过得太苦太可怜了!在最难以度日的吃食堂时期,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一幅幅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记忆画面,而几乎没有父亲的半点影子。
也许我外公外婆的基因特别强大,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像我父亲和至今仍健在的姑妈那样长得骨骼粗壮、身板笔挺高大;却反而遗传了外祖父家身材矮小还稍带驼背的形象。年少时感觉低人一等,吃了不少的亏。或者,这也是我父亲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也是父亲这辈子不怎么待见母亲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我的少年时期,我家有两个隐痛,一是父亲的右派,二是母亲有“暗病”。也许是公社化时母亲太过卖命落下的病根。我十一岁那年,母亲因膀胱结石大出血昏死了过去。抢救过来后,她身上多了一个物件——一根导尿管和一只橡胶尿袋。母亲从此失去了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而且会时常发炎、出血。贫病交加,加上父亲“摘帽右派”的身份,像三座大山压在我家头上,压得我们难以喘过气来。
从十五岁夏天下地的那一天起,我比大人们早出工,迟收工,拼命似地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一年到头,绝不会偷懒缺半天工。我家在东横河南岸“大屋里”的废墟上,有一块三分多的自留地,每年种两季水稻,以弥补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在轧米厂里比我空,一开始我指望父亲能干点自留地里的活。但父亲种田敷衍了事,是只“三脚猫”,后来,我就干脆不让父亲染指自留地里的活了。种水稻不能断水,那块自留地也是瓦砾滩,石头特别多,而且是块高地,关不住水。好几年的春夏两季,每天生产队收工后,我就东跑西奔地借水车,把父亲当年弃之若敝屣的那种手摇水车借来后,就发狂似地奋力车水。不车水的日子里,耘田、除虫、施肥、拔草……每晚总有做不完的活,直到县广播站当天广播结束,山顶上大喇叭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才扛着农具回家。就着家里人喝剩没有半点油花的咸菜汤,一口气把三碗米饭吞下去。
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子到了1974年,我家欠生产队的“倒挂”终于还清了。而且扭亏为盈,年初生产队的预算方案里,终于有了七十多元“顺挂”。我喘了一口气,这些年里,我似乎什么思维都不存在,什么也不去想,成了一架只会种田种地的机器。
但那一年夏天,母亲病了,我家的灾难又来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74年7月的一个晚上,电闪雷鸣夹着滂沱大雨,铺天盖地下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两天老是下大雨,前天中午时分,东山墙边的鸡笼里,一只正在懒窝的母鸡突然惊叫着逃了出来,父亲放下饭碗,见是两条三四尺长的大花蛇,大概窝被淹了,逃到了鸡笼中。父亲赶去拿铁耙,妈嘀咕着说家蛇是“龙”,打不得。天王老子都不怕的父亲,哪里管得了这么多,操起铁耙,向吐着信子的两条大花蛇乒乒乓乓砸了过去。一条大花蛇打死了,另一条逃之夭夭。也许真是中了邪,两天后,母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大半夜的隆隆雷声,吵得我睡不着觉。早晨沉睡中,我突然听到父亲在侧屋的甬道上低沉喊我:起来!阿强,起来!你妈不行了……一听到我妈,我从竹榻床上一下跳了起来,赶到正屋的父母床前。昏暗的灯光下,床前的痰盂中,是母亲体内流出来的大半痰盂浓浓的血水。父亲告诉我,这些日子里,你妈老是出血,看样子积石又多了起来,又得上医院做手术了。母亲还是跟往常一样镇静,听说去医院,连声拒绝:不去,不去!父亲吼了起来:你能熬得过去?你身上还有几滴血呢!父亲接着斩钉截铁地吩咐我:快去弄船,去浒山医院!
我摸黑敲开了生产队的仓库门,背起船橹拿了纤绳赶到船埠头。但队里的两只河泥船,已被一夜的暴雨彻底灌满。我使尽力气,飞快地戽干了船舱中的积水。一切准备停当,我问父亲:钱呢?父亲抓了两下头皮说,今年不是顺挂了吗?先向队里借吧。我又飞也似地奔到保管员家里,敲开门借了50元钱。我感觉手里的钱,重得像金子,为了这些钱,我疯了一样整整干了四年。但今天,却成了母亲的救命钱。我无怨无悔,但心头还是有些感慨。
大姐出嫁了,哥分家了也难以指望。我拉纤的脚步飞快但十分沉重,父亲摇着船,二姐陪着躺在籐椅上奄奄一息的母亲。我们沿着东横河向西,接着向北转入华家江,进入大塘河向浒山医院匆匆赶去。晚上的雨实在太大了,河水暴涨,我拉纤的纤担很难打过桥洞,父亲也只能把橹一放,弯着腰从桥板下钻过去。
浒山医院就在大塘河南岸,医院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河湾,我们就在河湾上泊了船。那时,太阳才刚升了起来。母亲的躺椅放在医院走廊上,她进入了半昏迷状态,导尿管中的血水,还在慢慢流淌着,一点一点滴在了躺椅边的痰盂中。父亲缠着刚上班的医生,医生询问了病情后,接着看了看母亲,脸色有些沉重地把父亲叫到了门诊室。父亲出来后,一脸阴沉,吓得我和二姐不敢问母亲的病情。父亲说,补了血再说。约摸一个多小时过去,一个高卷着裤褪,赤脚,两腿还沾着泥巴的姑娘匆匆赶过来找医生。姑娘胖乎乎的,看样子刚从水田里回来。医生一见她,就说抓紧。赤脚姑娘二话不说,找一把椅子坐下,一把捋起了衬衫的衣袖。医生也是话不多说,叫姑娘把盐水瓶搁在大腿上,说完就把一个大号针头刺进了姑娘的臂弯。姑娘的鲜血哗哗流进了她腿上的盐水瓶中,但她若无其事,眼都不眨一下。不一会,盐水瓶中的血浆快满了,姑娘侧脸看了瓶上的刻度,对医生喊道:够了,快点,我还要种田去。接着,姑娘接过医生递来的钱,一把塞进裤兜,头也不转一下,匆匆离开了医院。
四百毫升血浆,一滴滴流进了母亲的血管。母亲睁开眼,她那惨白的脸色有点红润了起来。我和二姐暗自高兴:母亲有救了!但痰盂中母亲的血水,滴得更快了。我们谁都明白,母亲虽然补了血,但只是权宜之计。当时的县级医院,无法给母亲做手术。
大雨过后,夏日中午的太阳又毒又辣。我、父亲、二姐谁也没有心思吃饭,心情异常沉重地在回家的路上赶着。我心中十分明白:这是凶多吉少,如果没有奇迹出现,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快到家门口,我发现大墙门口站着许多人,在七嘴八舌议论着什么。一见我们回来,都赶到船埠头问母亲怎么样,看我们脸色,谁都明白了大概。一位堂嫂凑过来告诉我:你家又出事了。上午好端端的,大水缸爆了。
亲族和邻居们七手八脚把母亲扛了进来,躺椅放在了正屋的前庭下。母亲处于半昏迷状态,好像沉沉地睡着了。
放在正屋前小天井的一只大水缸爆了。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接“天落水”做饭用的两只大水缸,就一直在天井中放着。昨晚下大雨时完好无损,却在上午的大晴天中爆裂了。地上留下了水缸爆裂时水流冲开的痕迹,更为蹊跷的是,除了相对完整的缸底,巨大的缸体彻底粉碎,散落在天井四周,竟找不到稍稍大一点的残片。屋内屋处站满了前来帮忙和看热闹的男女老幼,大家纷纷议论着母亲的病,多数以“九、缸、蛇”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我一下想起母亲是四十九岁,正是本命年,乡间传说中最为凶险的年纪。
我陷入到无比的绝望之中。这时,跑到附近化工厂给上海舅父打电话的父亲回来了。父亲这时已拿定了主意。我哥嫂和几个族中堂哥、堂嫂围上去,向父亲提出了做妈妈“后事”的事情。父亲愣了一下,接着脸一沉骂道:放屁!人还没死呢,我要送到上海去!
围在父亲身边的人都一脸茫然,纷纷看一眼在躺椅中一动不动的母亲,又惊愕地看着父亲,有胆大的问了一句:万一呢?……亲人死在外面,在乡间是件大不吉利的事情,听说会害子孙。

今日的鸣鹤古镇资料照片
少说两句!父亲火辣辣地瞪了一眼多嘴的本家族人,接着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救,送到上海去!父亲接着说了他的计划:现在是两点多,晚上五点左右有一趟余姚到上海的火车。用船送到余姚肯定来不及,只能去赶一趟三点半左右从浒山到余姚的公共汽车。有人提议:去浒山犯不着,万一赶不上呢,到横河去拦汽车更有把握。东横河河面宽,机船跑得快!
十万火急,拼死一搏。本家和乡邻们无条件帮忙。不一会,父亲跳上了抽水机船,亲自操舵。当时,抽水机船是乡间跑得最快的运输工具。父亲做过抽水机手,熟悉这一行当。
父亲开足了马力,水管口压上挡水板的抽水机船,向河面喷射出一股湍急的水柱,拖着那条去浒山医院的河泥船,在东横河上飞奔。河道上卷起了一道道浪花,不停地向前翻滚。到了横河街一个船埠头,众人迅捷地扛起躺椅,小跑着向汽车站赶去。
这时,一直昏睡着的母亲突然醒了,她一下知道了,居然硬撑着扬起了头,她叫道:不去,不去!父亲边跑边说:不去?你能做两世人吗?你会死的!母亲挣扎着想跳下躺椅,边说,不去,我真的死也不去,你饶了我吧……我突然心头绞痛,手脚发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平白无故地去死啊!平时,母亲最能忍受住痛苦,打针从来不会哼一声,而且把生死看得极其淡漠。我心头当然清楚,这几年母亲一直在暗暗自责,自己拖累了家庭。
没过多久,沙石公路扬起一股黄尘,去余姚的公共汽车到了。母亲又醒来了,还是挣扎着不想去上海。父亲由不得她,一把抱起挤进汽车。汽车带着我的一片希冀开走了,我望得老远,在心里默默祈求:妈,你千万活着,我还没有报答你。只要你活着,我做牛做马也好!
我感谢我的父亲,关键时刻是个铁打的汉子。即使真有鬼神,也奈何不了他!在当时的乡村,如果换了别人,就是十个母亲也会死去。是父亲的果断和不信邪,救了母亲的命。
之后,母亲磕磕绊绊又在这世上活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