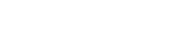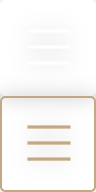1970年代的往事
徐志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鄞县一家队办胶木厂跑外勤,一年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外地接洽业务。那时宁波长途交通,大致是每天一慢一快两班火车,和一天一班有时两班的“上海轮船”。慢车直达上海,宁波站上午始发,全程耗时十余小时,票价6元;快车下午2点多发车,终点站杭州,到杭州无需出站,马上可衔接去上海的快车,到上海全程不到七小时,票价7元2角。而当时上海轮船通常傍晚开船,在船上睡一夜,次日晨到上海。轮船票价:五等统舱3元6角,四等舱4元7角,三等舱5元4角,二等舱7元2角。后来“繁(新)荣(新)昌(新)盛(新)”类新船加入申甬航线,多了一种五等卧铺,票价4元4角。宁波人讲实惠,火车与轮船比较,多数宁波人会选择乘轮船。
宁波这种交通格局,注定上海是宁波通向外省的跳板(那时宁波没有民航),无论去外省或返回宁波,人们多数在上海中转。
因为一年中有十数次往返沪甬间,我这个外勤,每次从上海返回宁波,肩挑手提像“跑单帮”,为别人捎带“上海物什(甬音为meshi)”。那几年,我为别人捎带的东西形形色色,啥脸盆热水瓶碗盏,糖果味精布料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宁波也能买到,但是人们就是喜欢上海货。那年代上海货几同优质商品同义词,比如脸盆(宁波人叫面盆),宁波只有单料货,拿在手里轻轻的没份量,远不如上海双料货脸盆“扎至(结实意思)”,且花样既多又漂亮。所以,村里有人嫁女,常托我到上海捎带“好看一眼”的双料脸盆。再比如糖果(宁波人叫小糖)村里小店就有,但是遇到婚嫁喜事,熟悉我的村里人常托我到上海捎买什锦糖。那时上海什锦糖有三种:1元2一斤的什锦硬糖,1元4一斤的什锦软硬混合糖和1元6一斤的什锦软糖。多数人选择1元4一斤的什锦软硬糖。捎带沉甸甸的糖果较累,但是只要别人相托,我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知道,但凡托我捎带这类东西,他们肯定权衡过与我关系的,认为关系笃厚才开口的。
那些年,让我捎买最多的是布料,这是因为浙江省布票在上海可以通用的缘故。当时,上海买“的确良”类的化纤布要上海工业劵,肥皂食糖凭卡计划供应,这些东西村里人是不会开口让我捎买的。所以,大家让我捎买的都是用浙江省布票可买的棉布。如果是捎买卡其布好办,只要问清颜色数量,明确是纱卡还是双面卡就行了。不好办的是女人们让我捎买的花布。女人们买花布没有具体要求,只是笼统提出花布“要好看一些”。这个要求,对我这个未婚后生来说是难题。在推托不掉的情况下,我只能“赶鸭子上架”了。到了上海布店,眼瞅着眼花缭乱的花布,我只能随便挑几种,按照各人给的尺寸剪买了。当时我想,挑的布花样让人不滿意,下次大概沒人让我捎买了。哪晓得“随便挑”的花布到了女人手里,她们个个都很喜欢,称赞我“挑花布生话好”。这一来我捎买花布的“业务”越来越多,有时竟达二十余款。遇到这种情况,我每次回宁波时,早两个小时到十六铺码头,就近在小东门“信大祥”布店,随便理出一大堆花布布匹,让营业员按我给的单子剪布——我只遵守一个原则:每种花布决不重样。即便这样,花布拿到村里,女人们还是很满意。当然,我知道我哪会挑花布,女人们满意,是因为上海花布设计得好。
我给人捎买东西是有原则的。比如捎买上海货问题不大,但是让我捎买外地核桃花生葵花籽之类的土特产,我只能谢绝。这东西宁波紧缺,即便有价格也贵。如果口子一开,恐怕我难以承担,这是其一。其二,有的东西长途携带还有风险。比如花生,安微六安农村每斤只三角左右,差不多只是宁波价格的一半。不过那东西属油料,当地管得紧,不让随便流通。一次,我们一行人去安徽出差,大家买了不少花生,结果被查抄了,最后三角一斤买来的花生被以二角四一斤的收购价收购了。这还算幸运的,只是亏了些钱。如果把你当投机倒把关上几天再罚款,那就麻烦了。
俗话说“管闲事淘闲气”,我为别人无偿捎买东西应该是“管闲事”,偶尔受点“闲气”也是有的。当时别人让我捎买东西,有不少人让我先垫钱,东西捎到后再算账。某次,有人让我捎买脸盆,谁知在码头上绳子断了,把脸盆给敲坏了。破损脸盆咋可给人,于是我只能闷声“吃进”。这件事不知咋地被托我捎带人知道了,他一定要付钱给我拿回破脸盆。最后,我钱倒是没亏,但无端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
还有一次,一个女人让我捎买一副女式大衣钮扣,为此,我专门跑了一趟上海城隍庙。谁想带到后,那人对钮扣不中意,说不要了。弄得我只好“吃进”这副对我一点没用的纽扣。虽然,一副钮扣值钱不多,但心里肯定郁闷,当然,该人也被我列入了“黑名单”,以后甭想让我再捎买东西了。
写下这些文字,突然感到那些我们曾亲历的往事恍若隔世。这些事情,莫说现在年轻人不晓得,就是我们有些老人,差不多也忘记了。这些经历,广义上大概也可以算作历史吧,历史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这就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理由。
202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