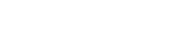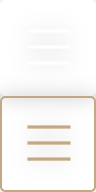雪的意象:小女孩视角中的战争与和平
谢志强
小孩眼中的雪是什么?谢志强念小学一年级时,每逢下雪了,就会跑出去,向天空张开双臂呼喊:下面粉了。他清楚是下雪了,只是希望下的是面粉,因为,他老是受饥饿的困扰。美国有一个小女孩,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下雪了,她惊叫:炸弹!炸弹!她为什么会把雪花看成炸弹?这仅仅是她第一次看见下雪。
关于“雪”,我想起一系列小说。川端康成的《雪国》以及以“雪”为题的小小说、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乔伊斯的《死者》(结尾经典的“雪”)、卡尔维诺的《迷失在雪中的城市》、帕慕克的《雪》、马尔克斯的《雪地上的血迹》、卡夫卡的《城堡》(K深夜入村时的“雪”)、王蒙的《在伊犁》(浪漫的“雪”,当时他在草原为主的北疆,我在沙漠为主的南疆,两地的雪不一样)……我罗列关于“雪”的小小说谱系,是表达一个想法,要摸清谱系,才能发现自己怎么写出独特性。这些均为成人写成人。且看儿童视角里如何表现雪。
这里想说的《雪》,是美国作家茱莉娅·阿尔瓦雷斯长篇小说《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之一章。那是碎片化组成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均可“独立”。多视角讲述女孩的成长故事。被选入美国“21世纪新文学经典”21部之一,美国“全民阅读计划”的4本图书之一。是与《芒果街上的小屋》齐名的成长小说经典(我曾提取过此书《许愿》一章,以《作家要寻找自己的一间小屋》评析过)。
由“女孩不再带口音”,已传递出信息——女孩的视角,母语的口音,这透露出小说要表现语言和身份的尴尬。这也是当代小说关注的存在的敏感问题。当今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文学,有一个突出特点:身份的边缘转为文学的主流,而且,释放出被压抑的声音,作家多为女性。如此,墨西哥裔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古巴裔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和多米尼加裔的朱莉娅·阿尔瓦雷斯,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女作家都属于拉美裔。包括印度裔作家裘帕·希拉莉等。若延伸到少数民族,有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这种有意思的文学现象,给我造成“阴盛阳衰”的感觉。
当我们谈现实主义时,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处理人物命运与时代变化的关系。朱莉娅的《雪》就很好地融合、处理了这种关系。不妨将它当成小小说——其实它具备了小小说的所有特点,又突出表现了“大与小”的关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小女孩眼中的小雪花,包含了大事件。
大事件,也是《雪》的大背景:古巴导弹危机——核导弹。那是苏美冲突的一个焦点,差一点引发核冲突。那是冷战激化的标志,也是苏联解体的伏笔。核武器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一次,但是,其恐怖的阴影却持续笼罩着全世界。我也感受过核武器的“阴影”。“深挖洞”——在戈壁滩挖防空洞,就是防原子弹。我数次做过原子弹的梦,后来,我想:原子弹投到大戈壁,不是浪费了吗?《雪》表现了居住在美国的小姑娘约兰达对核导弹的恐惧,导致她把“下雪”当成投炸弹了。小女孩把核导弹与炸弹混淆了。那是她到纽约的第一年,也是她第一次见识雪。
《雪》开始一段,作为唯一移民的小女孩——“我”被隔离开,坐在第一排特殊的座位上。身份的尴尬。与同学隔离,却与老师融合了。
《雪》重点写了小女孩和老师的关系,带出并引入核导弹的大事件和雪花的小事件。幸亏孤立中有像外婆的佐薇修女这位老师。不经意地点出了雪——这个英语的新词(未见雪先知词,知名先于见物,只知概念的“雪”,轻轻地安放这个细节作为伏笔)。而且混在别的新词之中。作者写道“她缓慢而清晰地念出要我重复的新词:洗衣房、玉米、地铁、雪。”
由若干生活中的英语词汇,扩展到报道的“大屠杀”,古巴的俄罗斯导弹,以及纽约的应对演习,电视上肯尼迪总统的担忧。茱莉娅就是从容地由“新词”的学习转入了时局的危机,把“大事件”引入。然后,简洁地由语言转入行动:学校的防空演习。顺笔点出了小女孩幻觉中的核武器的影响:头发掉了,骨头变软了。家中还数念珠祈祷世界和平。新词又出现:核弹、放射性尘降物、防空洞。还有老师的板书,画了蘑菇——将新词形象化。
《雪》贴着小学生的视角,在“新词”上紧张推进。读者感到了战争与和平的纠结。——小小说的空间开阔了。然而,一转:天气越来越冷。先写霜,再写雪——作者从容铺展着,时局转到气候,两者都冷:时局的雪,落在心里;天气的雪,在小女孩的眼中。潜意识地叠在一起——炸弹!炸弹!随后,小女孩大哭——吓坏了。
老师——佐薇修女像个守护者。小女孩视角中,“她朝我冲过来的时候身上的黑袍像气球般鼓了起来”,一个“鼓”字,炼得多妙,表明跑的速度和她身体的形状。然后安慰:“亲爱的约兰达,那是雪花。”还笑着纠正:下雪了。
女教师也像纯洁的雪花。那是爱的结晶。结尾博大:每一片雪花的形状都是独特的,如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代替的,都是美丽的。这也是师生之间的结晶。所有的叙述支持着“如雪花般的”这一句话。小说和人物都得以升华。
拉美裔的三位美国女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小说的诗性。我想,这也是女性作家独特的文学感觉吧?茱莉娅属于经验写作,其小说的素材来自经历。《雪》将冷与热、轻与重、雪花与导弹、战争与和平等小与大处理得如此妥帖,是小与大的经典范例。
佐薇修女这个教师的形象可谓爱的化身,温暖、慈爱。读茱莉娅的《我的英语》,从那非虚构自传,能够辨识出与其虚构小说的关联。其中,我发现了佐薇修女的原型。自传里,她的英语教师是伯纳黛修女——把粉笔断成两截,用力板书,写下简单句:下雪了。于是,茱莉娅开始想象雪,然后,“我在语言上着了陆……我走进了英语”。尤其是,伯纳黛修女训练其想象,有独特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写下小故事,“想象自己是雪花、鸟儿、钢琴、人行道上的石子,天上的星星。把自己当成一朵植根于地下的花朵,会是什么感觉?倘若云会说话,它们会说什么?……假设,只要假设……我的心飞了起来……”
我感到似乎颇有庄子梦蝶的境界——万物平等,天人合一。能见识茱莉娅小说中的假设,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假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