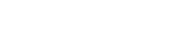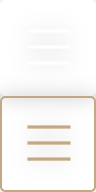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8第05期(总第二十期)
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回忆
文/鲁 冰
1943年初冬,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挑起内战,派出挺进第三纵队贺鉞芳部为主力,收编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为挺进第四、第五纵队,合击我浙东游击纵队,妄图亡我于四明山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多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果的情况下,浙东部队只好被迫起而自卫。自11月19日奉化北溪的大俞战斗和蜻蜓岗阻击战开始,至1944年2月25日茶坑战斗为止,历时四个多月,同挺进3个纵队、浙江保安团2个团,以及全部美械装备的5个突击营经过大小几十仗,付出重大的代价后,才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
这次反顽自卫战争,是在敌众我寡、内线作战和外线出击交替中进行,虽然没有打过出色的歼灭战,但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为后两年浙东部队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夜袭大俞村
敌挺进第三纵队有一个大队,1943年11月19日已进到奉化北溪附近之大俞村,企图继续北进,配合“挺三”大部队与“挺四”、“挺五”合击我军。我第五支队在大岚山区的蜻蜓岗做好阻击“挺三”、“挺五”的进攻。我第三支队当时驻在鄞奉边境地区,奉命出击挺三到达大俞的大队。我正好在三支队帮助工作。当时,战士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义愤填膺,士气高昂,一经动员,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傍晚,我三支队从鄞奉边境某地出发,夜袭大俞之敌。攻击作战任务分别是:正面由一大队负责,二大队负责侧翼佯攻并对奉化新昌方向警戒。我距敌驻地约20多公里,部队出发不久天就黑了,又遇上绵绵细雨,道路泥泞,行军极为艰难,20多公里路走了约5个小时,到达攻击出发点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一大队立即发起进攻,大队长蓝碧轩身先士卒,带队一下冲进敌营。敌人依靠靠山傍溪的有利地形,组织抵抗。我军英勇奋战,一个冲锋就突破敌防线,打到敌大队部门口,直捣敌巢穴。仓忙中敌向后山四散逃窜。我二大队从侧翼用火力阻敌,牵制敌人,掩护一大队进攻。结果因为敌在深山密林,夜里目标又不太清楚,大部敌人被逃掉了。前后战斗1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这一仗算是击溃战,但不过瘾。尽管毙伤俘敌近百名,敌酋大队长被我击毙,还缴了该大队长的一支手枪和一部分枪支弹药,然而我们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一大队的大队长蓝碧轩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打扫战场后,我军紧接着向鄞慈山区彻夜行军,黎明前经过鄞奉边境的商量岗,在山上休息时,侦察员报告山下东西两岙驻有“挺三”部队。司令部传令队伍作好战斗准备,原地待命。此时东方露晓,随着一轮火球冉冉升起,万道金光把山下村落照得明明白白。一会儿,村里吹响了起床号,附近各庄的号声也接着响起。大家手痒痒地握紧了钢枪,忘却了一夜行军的疲劳,轻了装,准备冲杀。“怎么搞的,作战命令还不下来?!”战士们都在悄悄地问。等了一会儿,山下庄里已经有人在行动了。这时,“三支向东岙,五支向西岙攻击”的命令下来了,部队立即行动,指挥所就设在商量岗的山顶上。
我部队刚冲下山,敌排哨就发现了,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我下山的连队势如猛虎,一排手榴弹就干掉了敌排哨。这时敌人一面紧急集合,一面向对面山上移动。我三支见敌人要抢占对面高山,连忙分成两路,一大队向东岙村攻击,二大队跑步向对面高山猛冲。为抢夺山上制高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我一大队冲进东岙村,捉了一些俘虏,其余敌人全往对面山上逃去。二大队继续向对面山上攻击前进,敌人拼死阻击,造成我军不小伤亡。当时整个山谷震荡着“冲啊”、“冲啊”的喊杀声。毕竟一夜行军体力消耗很大,而敌人却休息了一夜,体力比我们强,结果敌人先我抢占了山岗顶峰,居高临下向我射击。我二大队稍事调整队形,组织好火力,首先由四中队沿山脊向敌发起正面冲锋,六中队从左右两翼侧击前进,五中队集中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兄弟中队,副大队长陈洪才冲在前面指挥,部队前进十米,二十米,一百米,将接近顶峰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陈副大队长,他英勇地倒下了!部队继续向前冲,大队长,政委也一起往上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制高点夺下了,敌人被击溃了,丢下几十具尸体四处逃窜。我部捉了30多个俘虏,遗憾的是敌人的大部队还是逃掉了。
蜻蜓岗伏击
蜻蜓岗伏击“田胡子”(田岫山)这一仗,是12月1日清晨打响的,打得残酷,代价虽不小,战果却有限。
侦察获悉,田胡子亲率“挺四”千余人,对我四明山中心根据地烧杀掳掠后,经樟村、密岩回窜上虞老巢,将途经蜻蜓岗。蜻蜓岗是根据地中心地带,群众条件好,地形也有利,纵队首长决定在蜻蜓岗伏击田部。五支队埋伏于北山,三支队埋伏于南山。
大岚山上的迷雾,随着旭日东升而逐渐消散。来了!来了!一支由东北向西南的队伍,沿着山间小道缓缓而来。一队过去了,又来一队,人马真不少。战士们揭开手榴弹盖,架好枪,对准敌人,要痛打一番。后面的敌人还未进入伏击圈,突然一声枪响,接着呯呯嘭嘭就打开了。敌人被割成两段,后续部队掉头向来路退去,陷入伏击圈内的敌人也立即散开,抢占就近山头,组织抵抗,实施反冲锋,企图夺取南山窜逃。我三支队战士们用手榴弹、机枪回击敌人。北山五支队阵地前,手榴弹爆炸声伴着枪声,震撼了山谷,四处都在喊杀。三支队对冲上来的敌人,打了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击退并将其压回山腰里。田胡子这支老兵油子队伍,战斗经验较丰富,虽处险境,然队形不乱,节节组织抵抗,相互掩护撤退,还不时来个突然反击。
我战斗部队都往山腰杀下去了。敌军在反击中掩护撤退。在我三支队指挥所阵地上,当时只剩下余龙贵参谋长、纵队司令部作战参谋余旭和我,还有一挺重机枪和两个机枪手。突然,约两个班的敌人,从山坳中掉转头来向指挥所攻击,情况十分紧急。我们三人猛扔了三排手榴弹,一旁的重机枪也猛然向敌人扫去,第一批冲上来的七八个敌兵,被打倒了几个,其余都退了下去。这时,敌人在山腰的一挺机枪向指挥所疯狂扫射,我重机枪手负了重伤,幸好余参谋长是重机枪手出身,他迅速接过重机枪,调整好位置准备打击正在冲上来的第二批敌人。
第二批敌人冲上来了,有十几个人,余参谋长把机枪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敌人往上冲的通道上,我们又一排手榴弹,敌人丢下尸体又退下去了。接着,第三批又有十多个敌人在一个军官的强令下,往山上冲来。于是我们集中火力都瞄准敌军官射击,随着敌官倒下,敌士兵队形一下就乱了拼命往山下逃去。
在战斗间隙,我们坐下喘口气,拿出水壶想喝口水,余参谋长一见就喊,先不要喝!原来,重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急需水冷却,不然,待会儿重机枪就无法发挥威力了。我们赶紧把两壶水都灌进重机枪枪管。余旭在一旁问:“老鲁,山下怎么没动静了?我们下去看看?”我们二人同余龙贵参谋长商量,他说,“我也正有此意”。于是我们跃出工事,就往山下奔去。跑到半山腰,突然,从左侧射来一声冷枪,余旭“哎呦”一声,就慢慢向我身上倒来。我赶紧扶着余旭,让他慢慢坐下,只见他腰部血流如注,转眼间脸色似纸,我大声叫喊“余旭,余旭”,他没有说出一句话,面容一阵抽动就闭上眼了。余旭同志是浙江萧山人, 1942年冬从苏中调来浙东,是位年轻有为的军事干部,他牺牲时年仅25岁。
蜻蜓岗伏击战,虽把田胡子给打痛了,但战果仍不理想,没有达到成建制歼灭敌人的要求,敌人是击溃了,缴获也不少,但伤其十指总不如断其一指的感觉解气。
坚守横坎头
12月19日,田胡子为报蜻蜓岗遭伏击之仇,纠合“挺五”,竟给我军下了“哀的美敦书”,说是“限3小时内退出梁弄,否则用武力解决”,真是猖狂之极,岂有此理。
我军集结于横坎头,构筑工事,准备来次保卫战,看看四明山田胡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敌人两路向我进攻,一路由下管沿山北下,另一路经梁弄附近之后隙向丁家畈推进,横坎头阵地背靠大山,正面前沿旁有条大溪,溪后村前几座小山包堪为天然屏障,山上工事坚固,守卫的部队不论是特务大队还是警卫大队,都信心十足。田胡子陈兵于大溪对岸的山麓上,以火力威胁,又打机枪,又轰迫击炮,喊声震野,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在前沿的小山包竹树林里静静地观察,一点声色也不露。
从上午10点多开始,至午后2点多,敌人才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搜索前进,渡过了溪滩,占领了开阔地上的两座小高地。我机动部队要求出击,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在,他们一致说服部队耐心等待。不意由伪税警团刚反正过来的警卫大队大队长徐秀天等人忍不住了,说,“这欺人太甚了”,要求派一个排跃进出击一下。这个要求被批准,我们随即看了一次短兵相接的实战精彩表演。由大队副张义带队,第一班出了山包,一个个单兵以极其熟练的匍匐动作,飞速通过开阔地,看准前面的坟包、土丘,一个跃起,箭似地射出,占领有利地形,再看清前进通道,继续跃进。第二班,第三班相继散开跟进。只见田野上20多个单兵,娴熟地利用地形地物,跳跃前进。要不是敌方不断的枪击,真以为是在上军事课搞野外演习呢。他们接近敌人所占的土包后,三个一群,两个一组,架起枪来猛烈射击,火力非常集中,敌人被打倒几个后,其余的拔腿就跑。敌人溃逃了,怕战士们追过溪滩,指挥员下令吹号收兵。
太阳已到了下山的时候了,敌方光用迫击炮轰,看来这是收兵的信号。纵队首长聚在一起商讨晚上派一部分兵力出击一下,正在谈得热烈的时刻,忽听“嘘嘘”的弹道声由空而降,首长们判断是迫击炮弹,有的还未来得及卧倒,一颗炮弹不偏不倚在人群中间的空地上“噗”的一声钻入土中。我们都在防备爆炸的震荡,担心又有几位同志要遭难,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嘿!奇迹!一秒、十秒过去了,那颗已经入土的炮弹竟然没有爆炸!首长们立即易地继续商讨。有人说,“这是马克思在天有灵”。
天黑了,刘亨云参谋长率领五支队一部,由梁弄杀出去,沿途没有遇到阻挡。到了敌区一山包上,忽闻人声喧哗,手电光照上照下,似在崎岖山路上艰难地跋涉。刘参谋长派侦察员抓来条“舌头”,一问,原来是“挺五”的军官团,他们掉队了,正在找路。刘参谋长急中生智,想出一计,与部队领导商谈好,立即分头布置。刘参谋长冒称“挺五”的参谋,用北方口音喊道:“你们是军官团吗?怎么搞的,队伍拉得这么远,叫团长快点来接受任务。”有个50来岁的军官闻声前来,问“又有什么任务?!”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几个人一下子围住他,枪口直指他的身上:“不许动!”, “命令你的人过来集合!”为了保命这老兄乖乖地下令部下集合,200多名军官、10几名士兵被集合起来,服服帖帖地当了俘虏。
这个军官团,是我们自卫战争打响以来成建制歼灭的第一个。
奔袭章家埠
1944年元旦后不久,部队两次奔袭章家埠。
当时的战斗部署是:三支队主攻章家埠,五支队攻下汤浦后向章家埠合击,特务大队攻击章家埠的防御体系姜山制高点,得手后合击章家埠。
第一次奔袭章家埠,我在特务大队二中队。二中队的任务是进攻章镇东北的姜山,占领阵地工事,警戒阻敌,保卫司令部指挥所。
战斗在凌晨发起,打得很顺利,二中队配合一中队迅速攻占了章家埠的屏障东北姜山,歼敌一个排。一中队由队长周振庭率领向章镇突进,二中队占领山上所有工事,掩护一中队前冲,警戒敌人。
章镇是“挺五”司令部所在地,经过多年经营,筑有大小不等的明碉暗堡。我三支队和特务大队攻入镇上,敌作困兽之斗,拼死抵抗。战斗至上午10时左右,缴获了不少弹药,抓了几十个俘虏,但也传来周振庭不幸牺牲的噩耗。
我们坚守在山顶上,对战斗的进展看得很清楚。当时何克希司令、刘亨云参谋长都在我们阵地上观察。汤浦的敌人,凭借曹娥江顽抗,五支队打得不很顺手;章镇之敌调来增援部队组织反扑,镇上打得很激烈。敌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向我二中队阵地猛扑,妄图夺回姜山。何司令、刘参谋长命令坚决打退敌人进攻,坚守阵地,保卫指挥所安全。二中队依靠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居高临下,三次组织反冲锋,把敌人击退,我们有枪榴弹轰击,以神枪手发射冷枪,指挥官被击中倒下后,手中的指挥旗被扔在一边,数十名敌人被我击毙击伤,进攻敌人很快退去了。
至午后,战斗呈胶着状态。在敌占区不打速决战,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自己的。纵队首长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回梁弄一线休整。
第二次奔袭章家埠前,特务大队已编为五支队第三大队了。这次没有大打,而是着重抄了“挺五”的后方,把蒋介石新拨给的弹药,我们不打收条,收缴了一大批。战士们子弹带装得鼓鼓的,身上的衣袋里也是满满的,他们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好了,蒋介石给我们送来了子弹,下次打起仗来,我们一定把弹头还给他。”
夹塘阻击战
“挺五”为报我军两次奔袭章家埠之仇,配合顽军突击营,向我中心地区梁弄等地进犯。为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打击敌人,我五支队由刘亨云参谋长率领,处于高度流动中。1944年元月31日,我军经洪家岙、永和市等地,到达上虞和余姚交界的夹塘镇。
早晨到达,部队很疲劳,休息了一个上午。午饭后不久,“挺五”约两个营的兵力,从永和市方向来袭击夹塘。我军警戒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其他部队则在原地做好战斗准备。
夹塘,是个小集镇,居民有几百户,街上商店不少。镇外地形是一片平原,而从敌人袭来的方向,却有一座高约100多米、宽约50多米、长约三四百米的高地,很像夹塘镇的一座屏风,高地上原挖有战壕,筑有碉堡。这个正面阵地,支队部决定由三大队八中队担任阻击任务,七中队、九中队集结在高地两侧作为机动。
敌人开始来势汹汹,先是一阵迫击炮轰击,继用重机枪猛射掩护,约两个连的步兵,呈扇形向我阵地进攻。我军沉着应战,当地人进到我阵地前二百米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其余的,有的往后逃,有的继续前进,大概有五六十人窜到了我阵地前方30多米处,坚守高地的八中队的同志们,一排手榴弹泰山压顶似的投向敌进攻队伍, “轰、轰、轰、轰!”敌人丢下了十多具尸体和十多名伤兵掉头鼠窜。
敌人组织的第二次冲锋就没有第一次那么猛了,士兵们畏畏缩缩,有的简直就是在爬行。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敌军中有个骑马的军官,强令士兵们冲锋,但是刚刚到我阵地前二百米处,我机枪一阵点射,步枪一个排放,敌人就停下不敢再前进一步了。过一会在那个骑马军官的威胁强令下,敌人第三次向我发起进攻。这次,敌人向我阵地“游击”,约有四五十个敌人呈散兵队形跃进,当他们进到我阵地前30多米处,又是一排手榴弹似流星雨般落在敌阵,我神枪手瞄准射击,毙伤敌人十多人,其余的一溜烟地溃逃了。我七中队、九中队奉命从两翼出击,趁敌狼狈逃窜之际一个猛冲锋,敌人全线崩溃。八中队亦相机出击,一直追到永和市。
追击的部队追了10多里了,天也渐渐黑了,一批俘虏和缴获的物资急需处理,大队长命令停止追击,司号员吹起了收兵归队的集合号……
“挺五”张胡子(张俊升)妄想乘人之危来“剪羊毛”,结果把“剪子”都赔了。夹塘一仗,打得张胡子丢盔弃甲,遭了重创,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
血战前方村
二次奔袭章家埠后,部队想去双江溪与金萧支队会师。军事意图是跳出内线,转入外线作战,以便调动敌人,寻找敌之弱点,歼敌一部以击退敌军之分进合击。期时四明地委来电,说梁弄一带中心区敌军全已退走,建议部队返回根据地。为此部队回师梁弄,期间在部队抵达梁弄北部山区的南黄、茭湖时后,曾与国民党新派来的美械装备突击营遭遇,因敌情不明我军稍微接触一下就撤出战斗,至杜徐、袁马一线休整。
几天后,在深入侦察后获悉,“挺四”田岫山部有一部分部队,仍驻扎在距梁弄西南十多里的前方村。当时以为前方村是个弹丸之地敌方不会有太多的兵力,认为我主力三个支队集中一起,吃掉田胡子不成问题。于是下达作战命令:入夜包围,凌晨攻击。
然而攻击一开始,却打得十分激烈。敌人依凭坚固的工事,利用阵地前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轻重机枪,猛烈扫射,杀伤我进攻部队,阻止我前进。我进攻的通道,恰好选在敌人火力网内,部队每前进一步,都招致伤亡。五支队的大队、中队两级干部伤亡最多。尤其是政治干部,从大队的正副教导员到中队的正副指导员,伤亡近10名,排以下的干部战士,伤亡数百名。这是浙东纵队战史上遭受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部队攻不进敌阵地,伤员不断后送,天快亮了,敌方突击营赶来增援田部,战斗难以持续下去。为此,纵队首长果断下令撤出战斗。
前方村这一仗虽打了败仗。但战火险境面前,共产党人革命战士都高度表现了英勇不怕牺牲的精神,从支队、大队到中队的军政干部,没有一个不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把生的可能让给别人,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仗没有打好,部队损失又大,我们撤出战斗后,敌人又尾随追击,部队情绪波动很大,干部战士埋怨很多,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则悄悄离开了部队,也有一些同志主张和敌人再拼一下,死也甘心。纵队领导针对前方村战斗失利和部队思想活动的情况,召开了军政干部紧急会议。针对广大指战员提出的是:“为什么进攻通道选择在敌人火力网内?”“侦察参谋干什么的!”“我们打了一次糊涂仗!”等意见,经过检讨、解释,总结教训等统一了指战员思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打好下一仗的问题上。部队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以崭新的面貌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茶坑遭遇战
自从前方村战斗受挫后,四明山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顽军以5个突击营3000多人为主力,纠合浙江保安两个团、“挺四”、“挺五”两个纵队,以及当地的一些土顽部队,四出骚扰,破坏我后方医院、工厂等后勤设施,抓捕地方工作干部,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清剿”,妄图消灭我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打击敌人的狂妄企图,浙东区党委制定了“分散活动,牵制敌人”,“坚持四明,巩固三北”的方针,决定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位领导同志率领司令部、政治部、教导大队和第三支队渡过姚江去三北;刘亨云参谋长率第五支队和纵队警卫大队,配合四明自卫总队坚持在四明山与敌周旋。
前方村战斗之后的半个月里,敌人猖狂至极,在我们根据地里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们地方干部十多人,部队派出从事民运工作的几个女同志,均遭这些敌人搜捕送往天台关押。中共鄞县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同志,被浙保二团逮捕,敌人用酷刑逼供不成,将她绑在樟村街上一电线杆子上,一刺刀一刺刀地捅,迫她投降。李敏同志不愧是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刺刀下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1岁。
为了打破敌人“围剿”的部署,刘参谋长率领的第五支队和纵队警卫大队,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有时长途跋涉,有时一日两易驻地。2月25日,我军开始秘密往鄞奉边境转移,以求跳出内线,转向外线作战。部队到了奉化鄞县交界的穷乡僻壤——茶坑。茶坑是个很小的村子,住户不到10家,可是处在高山之巅,周围都是崇山峻岭,悬崖陡壁,山坡上有一块小小的园地,种着杂粮和蔬菜,山上竹茂木盛,要不是战争,此处的宁静,堪与陶公的桃花源相媲美。
部队在山坡上休息做午饭。支队副参谋长张季伦来到我们八中队。他是个爽朗豪放、幽默达观的人,一来就学我的家乡土话开玩笑。我问他今天要转到哪里去,他说待各路侦察员回来看情况再定。他要我们抓紧做饭,吃饱待命。他正要走,两个从鄞江桥方向回来的侦察员报告说,浙保一个团几百人,正往茶坑行军而来,队形散乱,没有什么战斗力。张迅即带着二人向刘参谋长报告敌情。还有几位侦察员没有回来,怎办?经与支队首长商定,先派三大队七中队、九中队到浙保敌人来路上设伏警戒,后又派一大队、二大队前往埋伏地区待机歼敌,警卫大队和我所在的八中队占领制高点警戒西山我们的来路。部队尚未吃完饭就进入阵地了。
仅仅一会儿,只听到东山下炮声隆隆,机枪哒哒,手榴弹和步枪混杂齐鸣。看来浙保已陷进我埋伏圈了,大家都期待着打个胜仗,杀杀敌人气焰,为牺牲烈士报仇,扭转被动的局面。
东山下枪声还在炽烈的交织着,西山下又发现敌人如蚂蚁似地向我防守阵地涌来。这是国民党的突击营,算得上是我们的对手了。中队长吕芳和我当即命令全中队做好战斗准备,手榴弹揭盖,子弹上膛,3挺机枪紧紧咬着敌人
警卫大队也进入山顶制高点的阵地,我八中队防守一条陡峻而狭小的山路。我们的阵地就在高达20多米的悬崖上,敌人要想上来得攀爬20多米的梯级小道。我们待敌人靠近200米处时,用机枪步枪齐射,敌人冲到悬崖脚下欲攀爬梯级小道时,集中投掷手榴弹杀敌。这种战术是因地制宜的,很能奏效,敌人冲锋五次,全被我们击退,敌人丢下不少尸体和伤兵,向来路退去。我八中队从冬日当午战至日薄西山,整整打了五个多小时了,无一伤亡。
敌人溃退了,山下已看不到敌人,我们方坐下来休息。就在这时,警卫大队防线的山坡上枪声大作,原来敌人见攻我八中队阵地受挫,便迂回到警卫大队阵地那边去了。突然,敌人在我侧翼山坡上用多挺机枪集中向我阵地开火,一下子,我身中4弹,脚背擦伤,右大腿被敌人达姆弹击中,身上血肉模糊,两条韧带被打断,拉得很长,挂在棉裤外,腿上留下比手掌还大的伤口,左胸部中2弹,我当即狂吐鲜血,意识中闪过“老子今天就革命……”“到头”两字都来不及想,就昏迷跌倒。待我甦醒过来,发现在我身旁的副排长中弹牺牲。两个战士要扶我下山包扎,敌人又集中火力射来,一位战士负伤,我左臂上关节和臂膀中关节又各中一弹,左手就无力动弹了。我要战士回去坚守阵地阻击敌人,自己咬紧牙,忍着痛,用右手左脚支撑,爬下山去。
到了茶坑村上,老百姓已跑光,大部队已转移,留下八中队作掩护最后撤退。此时,暮色降临,中队长吕芳带着部队撤下来,见我还躺在村上,急得到处找门板,没有;做担架,来不及,吕芳命令四个战士抬我走。这怎么行呢!眼下最需要的是战斗员,不能为我而减弱部队战斗力!但是,从山上到山下的收容所要走7里山路,我没法走,也不能背,怎么办呢?最后吕队长决定,由小通讯员苗湾扶着我右手,我伏在他肩上,一瘸一拐地随着部队走下山去。一路上几次想躺下不走了,因为实在走不动了,整个身子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只有脑子还清醒。最后,还是靠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全身的疼痛和无力,终于坚持到了收容所。
部队连夜转移,我们几十名伤员,包括支队参谋长贾平同志,由卫生队和政工队的同志负责,抬到鄞江区的后陈村,由一位保长陈XX给我们“打埋伏”在一座靠山坡的古庙内。因发高烧,谑语不断,同住一室的其他伤员都觉得我没有救了,有个从伪军中警团反正过来的警卫大队的战士,四川人,是个老兵,很有经验,在我高烧谑语时,将一片甘草塞在我口里,顿见成效,我慢慢地就安静下来不再喊叫了。隔日我清醒过来,他告诉我,当兵的一定得带点甘草片,负伤后含在嘴里可以起到止渴生津、安神镇痛的作用。
我们伤员尚在敌人包围圈内,敌人正在到处搜剿。有一天下午,只听到一阵枪声,轻伤员和能走的,都紧张地潜出庙门往山上躲藏,只有我和贾平等重伤员,根本不能动弹,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静静地躺着,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一直到天黑了,那位保长手提马灯,带着10多个人,几副担架走近我们身旁,悲愤地说“真罪过,浙保今天下午到村里搜查,有十多个住在村里的伤员同志,被浙保发现抓出来,就在晒谷场上一个一个用刺刀捅死了,惨极!浙保还想上山到庙里来搜,幸好山上三五支队有十几个人打了一排枪,打伤了他们几个,这伙人吓坏了,不然你们就危险了。”保长说:“今晚把你们转移到山上,隐藏在柴草丛中。你们放心,饮食我们一定负责搞好。现在担架来了,就动身,怕敌人再来就不得了。”我们反正也不能动,一切听候他们安排,生死置之度外。
深夜,我被抬到一座山上,同去的有裘奋同志,他脚负伤,不太重但不能行走。山上有户人家,他们非常关热情地接待我们,还熬了一碗米汤给我喝,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第二天清早,山上还看不见太阳,夫妇俩抬起我躺着的担架,把我送到山上更茂密的草丛中掩藏起来。俩人每日轮流给我送来米汤喝,那时我只能吞咽液体,其他食物根本无力咀嚼。他或她来时,都装扮成上山砍柴模样,以免暴露。我躺在山上,日享阳光的恩赐,夜体霜露的滋味。讨厌的是苍蝇麕集,我又无力拂赶,伤口肌肉全在腐烂,臭味令人恶心。
大约过了3天,那位善良的女主人,突然来告诉我:“三五支队弟兄来救你了,他们马上就来。”我木然地注视着她,脸上极力地想露出一丝笑容来报答她却力不从心。她红润带点黛色的脸上,显得很激动,两眼噙着泪花,很有歉意地说:“我们原想每天晚上把你抬回家去,好让你少受点风寒,但他们说不好而没有动,让你在山上受苦了,实在对不起!”我无力说话,又无力露笑,只是口角微微一动,两行热泪刹那间泉涌般淌了下来:多好的人啊,我感激还来不及,那会怪你们呢!没有他们的照顾和保护,我还能救回去治好伤至今仍活在世上吗?人民的大恩大德,我是终生不会忘的。
1960年前后,我曾专程到鄞江区后陈村找过那位保长陈XX和山上的那对夫妇,欲向他们表示一下当年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可是非常遗憾,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过许多伤员的陈XX和那对夫妇,都没有找到。据说陈XX早已去世,山上的夫妇俩也不知去向
到后陈山上营救我们的是林一新大队。他们把我从山上抬下来,经过鄞江区樟村送至石岭支队部。时近午夜,接待我们的同志仍在等候着。第一个来看我的是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唐炎同志,他表示了亲切的慰问,接着盛林医生来给我剪开包扎已过七天的纱布,一股冲鼻的腐烂臭气,使人恶心万分,蝇蛆在满身蠕动。在身负这样的重伤,经历了这样残酷的七日七夜,在草丛中睁目观青天,闭眼黑万千,度过这九死一生的时刻,一旦回到自己部队,见到熟识的同志,心潮起伏,情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经过盛林医生、护士的精心清理,夹出伤口里的蛆,进行消毒敷药,换了新的被褥,当夜就转送后方医院,因左臂上一颗子弹折断了臂骨却嵌在骨内,伤口都已发炎,得赶紧手术治疗。
到了后方医院,经一位姓虞的医生为我动了手术,右腿上割去了烂肉,开刀取出骨头碎片;左臂全麻开刀,取出弹头,将断骨接上。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断骨接得不太严实,伤愈后左手比右手短1厘米,造成我终生的残疾。经过医生护士们的精心治疗和看护,不到半年,我又生龙活虎地回到了部队,继续从事锄奸保卫工作。
茶坑这一仗是个遭遇战,敌人在分进合击中正好同我们在茶坑相遇。尽管敌人打着消灭我军的如意算盘:先是三个月解决,继而“清剿”围攻,后又分进合击。但茶坑一战,现实狠狠地教训了敌人:人民的军队只要不离开人民,是永远也消灭不了的!任何倒行逆施,妄图消灭人民军队,只能是痴心妄想。茶坑一仗,我军虽付出了相当代价,但打痛了突击营,重创了浙保,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我军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