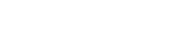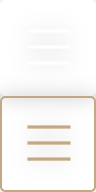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8第06期(总第二十一期)
2019第01期(总第二十二期)
寒冬赏梅缅怀父辈
——纪念项耿逝世两周年暨徐英就义七十一周年
文/陈诗斯
一、赏梅喻志,终身铁骨
大寒季节,蓉城虽没江浙“风鸣北户霜威重,云压南山雪意高”的寒冬景色,却是天蒙蒙、亦冷丝丝的感觉。我家坐落在城南,楼盘占地不小,住户达四千多家。楼前后的景观为中西式,布有水池,置有亭阁,植了树木,种了花草,显得格外宜居。我国自古有“梅花绕屋”或“登楼观梅”雅韵,院内中庭右侧水池旁,栽种了众多梅花。每当大寒时节,梅花盛开了,花瓣娇小玲珑,一簇红色的,如烈焰艳丽;一簇白色的,如洁白雪花,特别吸引眼球。
遭遇“文革”
也许,受到父亲喜爱的影响,我每当走到梅花前,就忍不住停下脚歩,仔细观赏起梅花来,自然也会思念起父亲。家里兄妺多,我从小随祖父母生活在老家慈溪观海卫。听母亲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经济拮据,父母把我祖孙三人接到湖州。那年,家住在海岛堂里,一栋独院小洋楼。据说,包括我家小洋楼的那片西洋建筑,建于1902年,由美国传教士韩明德用庚子赔款的钱,修建起红砖砌就、西欧风格的教堂,及其周围东吴附中与湖郡女中校区楼房。那独搂小院,原属传教士宅院,楼高为二层,我家住底楼。说是单独院落,却连接着教堂,院子还算大,栽有许多树木花草。
当年,小院隔墻连通毗邻大院,大院有三个嘉兴地委直属单位。西洋式高楼为地委党校,红砖洋楼为地区干部进修学院,红砖教堂为地区电影公司,可称机关大院。有资料显示,那时整个嘉兴地委机关干部最少时,只有200多人,且许多干部办公与生活都在一起的,此,说是独楼小院,其实是生活在大院子里。少年时那场政治运动,把大院原本平静的程序给打破了,有了极不平静的政治喧闹。“文革”初期,院内成了串连红卫兵的接待站,随后大字报贴满院内外,后来又成造反派争夺的战场,双方棍棒刀枪全都用上了。尤为可怕的是,机枪竟然架到我家二楼窗台上,枪口直对党校那栋楼,攻守双方群情激昂。虽说我已是少年,会看打倒谁或批判谁的大字报,也听到他们高呼着打倒父亲口号,但还弄不懂运动的道理。这一切已悄然改变了我家的命运,不久我们就搬离了那栋独楼,离开那个大小院落。从此,厄运降临,受尽屈辱。
那是1968年8月,父亲已隔离审查一年有余,有一天早上,家里突然来了许多机关造反派。这些人气势汹汹,不容商议,还不时喊着口号,并限令我家和同楼受审查的时任地委宣传部负责人,俩家限于当天搬离。我和长兄立于门前,真是少年虎胆,亦年轻气盛,怒视来者,据理要求他们,拿出父亲的组织结论,否则拒绝搬家。虽然,母亲是抗战老兵,腰间别过枪,战场带过兵,不怕生与死,可称当年女中巾帼。但是,母亲那年患有乳腺癌,刚在杭州动手术,且回湖州时不长,身体还十分虚弱;亦上有俩老人,下有7子女,一家共有11口人。母亲感到事发突然,不清楚如何安置?此时,在大姐搀扶下,母亲走到室外,面对凶恶来者,仍平静地问清原由。母亲回到房间稍许,就叫过我和长兄,十分痛苦地流着眼泪说:“你们父亲可能有工作错误,群众可能不理解。我们要相信你的父亲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我们也要相信人民群众啊!现你父接受审查不在家,你妈刚动手术,你俩是家里男孩子,要帮妈妈挑起这个家,我们要服从组织决定。”我与长兄,虽排行有先后,岁却仅差一年,是年15与16岁。听了母亲一席话,我俩好象懂得了许多,既不忍母亲的流泪,亦痛惜母亲的病痛。从现在眼光看,那时极为可怜啊!这样一大家子,匆忙收拾衣服,整理杂物柜椅,我踩一辆三轮车,长兄拉着一辆平板车,居然装不满全部家当,并在他们监视和威逼下,搬迁至眠佛寺街39号机关宿舍。
新搬入的庭楼,是中西合璧建筑,住有30多户人家,共有200多人,其中青少年和老人占多数,机关造反派也不少。那时造反派头头,明知我家人多,却有意迫害,故意刁难,安排窄小两间厢廊房子,合计22平方米面积。根本安顿不下,实在无法啊!兄妹们安顿好祖父母和体弱母亲后,在庭楼两进深间,厅堂靠我方一侧的过道,用凉席围起一个空间,安了两个床铺,置了烧饭煤炉,放了水缸杂物。平时,那个过道每天早晚,有上百人进岀;冬季,浙北极为寒冷,过堂风吹过时,直往被窝里钻,冷得难以入眠。长兄同学周思学的母亲看到我家遭遇,其母十分同情,让长兄睡到她家,与其儿同席一床,不久我也过去借宿。同年9月,奶奶忧郁过度,腹痛不止,经查为肿瘤,由大姐陪同,去杭州开刀摘除。次年12月,祖父病重,想见父亲一面,我们向组织提出(当时接待为陈良宇,时任项耿专案组军代表,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且被拒绝。不日,祖父对我们说:“不曾想到,杏根革命到如此地步!”带着对世事不解,在忧伤中逝世。“文革”后,方知是原来为父亲开了多年车的司机,当上地区机关造反派头头,取得了占有“洋楼”的权力,且搬进那栋独楼。当父母得知是那个司机时,父亲坦然听之,母亲却震惊不己。这个曾经是我家的常客,父亲对其是如此的信任,我们兄妹对其视同是亲人的人竟然会这样。
新迁入的那个大院,邻居有机关干部或工人,政治态度的不同,对我们冷热和迫害也不同。由此,让我兄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刚开始,我们的搬入,街坊邻里感到“新奇”,一些有“造反”倾向的邻居,不仅仅“警惕”我们,甚至怀有“敌意”。
该院落是民国湖州大户人家的民宅,其后进庭右侧后门,有廊檐过道,连接后花园。园中有太湖石垒成假山,假山临着池塘,顶端置有凉亭,石道空间可穿行,着实让人感到江南庭院建筑的优静雅致。假山前面有块坪地小院,植有树木花草,令人难忘的是两颗高大的梧桐树。梁园虽好,却不是我们的安居之地。夏令时,树下本可成为纳凉之地,我们搬入那年却成了“批斗”场地。在我看来,每周六晚上,举办的家属“批斗会”,是“造反”倾向的机关干部,专为我母亲设计的,而张明阿姨(时任地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陶清夫人,小学老师)纯属陪衬。会上,有些机关干部犹为积极,工人或家属基本是凑热闹,子女小孩均系看稀奇。我家后窗台,可看到那个“批斗现场”,有些机关干部领头坐在前面,同院家属们围坐在旁边,同街邻舍站在周围,每次围看有不少人。有些组织者明知母亲刚开过刀,他们却追求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表现”,仍对母亲釆取严酷“批斗”。每当我看到母亲,拖着病弱身躯,站在自带小板橙上,与张阿姨一同遭受批斗,真的心如刀割,万分难受。是日,打扫大院是体罚常用的手段,自然亦加在母亲身上,勒令与张阿姨一起扫地若大庭院。这时,母亲很坚强,仍鼓励我们,且安慰祖父母,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母亲有从军传统,且善团结群众,一早起来,就打扫起庭舍。我祖父生来勤快,虽己身体病弱,还不时帮衬母亲打扫,我兄妹也助上一臂。时间一长,与邻和睦,同宅融洽,相互尊敬,交往友善,所谓组织措施,也就形同虚设,反而引起邻里的同情。记得搬入次年冬季,父亲隔离审查,母亲去干校劳动,年长哥姐离家下乡。祖父丑寅时辰逝世,奶奶哭声惊动邻里,隔壁工人大叔阿姨极为同情,知我弟妹均不懂丧事料理,即帮助祖父穿衣处理后事。那是我家最艰难的时刻,能有人相助,实属难得啊!至今想起,兄妹仍然对好邻里,心存感激之情。
品格庭训
不过,让我至今难忘的,还是那棵独楼庭院前的腊梅。寒冬来临,天寒地冻,腊梅却绽放了,缤纷地开出黄色花朵,分外的妍雅,还飘来阵阵清香。这时,父亲会顶着寒风,时常站在腊梅前,颇有兴趣地独自观赏。有时也会把我们兄妹叫到跟前,科普起梅花的知识,说梅花有多个品种,原产地虽有不同,花期也有先后,但品质却是一样的,可谓“梅花寒冬开,独放百花前。”又假借赏梅,比喻起为人道理,启发我们要有梅花一样品质。梅花象征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神。你们的人生,也要有梅花那种迎春吐艳、凌寒飘香、铁骨冰心、奋勇拼搏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做一个有益社会的正直人。在我观察中,父亲就是按照这种品质要求自己的,也是父亲对人与事的评判标志之一。
父亲不光喜欢观赏梅花,亲近梅花,还喜欢画梅花。那个时候,父亲时常岀差,工作空暇,喜欢逛当地旧货书店,买些字画书籍,其中就有梅、兰、竹、菊的画谱。只要在家,爱在灯下3
摆上旧报纸,喜欢练字摹贴,颇为认真练习。这时,我就倚在桌前,看着父亲临摹作画。在我看来,父亲虽喜欢画梅和竹,但对画梅更有偏爱。有时,还给我讲些画“瘦骨之梅”的技法,手把手传授运笔或用墨,这些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据长兄陈赤宇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在杭州遇见过丰子恺,曾向其请教画梅花技艺,丰老随赠一幅梅花画。该画体现了丰子恺“尚质书风”,笔墨不多,画面简约,画有梅石。父亲崇尚质朴审美,十分喜欢那画。可惜,在“文革”中,我家被先后抄家五次,连同郭沫若、吴昌硕、潘天寿等字画,还有周恩来总理关于嘉兴专员公署专员和邓小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处书记的两份亲笔签名任命书,一并被造反派抄家拿走。从此,父亲再也欣赏不到那画的梅石之美,更感受不到那画中的时代书人精神气质,真的始终婉惜不已。
父亲的艺术修养,应该来源于自身聪慧和孩提时代所受的良好教育。父亲岀生于上海,从小生活在殷实家庭,发蒙在沪上巡道街东段林家园私塾(同乡富家子弟),后在大东门新制学堂求读,师资择优选聘,教学甚为严格,学业胜于初中,且音律演奏皆通。“文革”以前,那时流行《红梅赞》歌曲,我们兄妹也崇敬英雄人物——江姐,加上曲调优美好听,常喜欢跟着学唱。父亲能拉二胡,也会吹箫,有时会凑过来,与我们一起拉吹一曲《红梅赞》,父子显得格外深情且愉悦。
铭记操守
“文革”期间,父亲被猜忌,先后关押或审查7年多,遭受磨难,受尽委屈,家被“扫地出门”,子女歧视羞辱,祖父忧伤死去。此间,我目睹了父母受迫害,自已遭受株连停学。更为不堪回首的,1969年8月,我妹妹陈赤锋因小事与同龄邻居争吵,引起两家少年动手争执,那位机关干部邻居夫人,立马将此上升为“政治事件”,竟携4子女到地委机关,聚众高呼口号,张贴起大字报,指控我为父亲复辟。我兄妹时年仅14至16岁,就经历了社会政治压力,一度公安约谈调查,一时闻传湖城,惊动机关上下。不久,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下乡塘甸公社农村务农,后去襄樊市入伍参军,走上了自己人生道路。
然后,与父亲聚少离多,再也没有看到父亲画梅花、也没有听到父亲拉二胡或吹箫了。假设没有“文革”炼狱经历,父亲可能成为有一定造诣的业余画家。虽然,浙江省纪委在1988年,撤销了对父亲的“政治错误”定性结论。不过,父亲想弄清楚自己到底错在那里,一直向党组织申诉,直到逝世前,都没有人能告诉他,父亲也就带着遗憾走了……虽说作为中共党员,为党的事业,个人可以受委屈,但社会公德不能受扭曲;个人可以受不公,但我党实事求是的党风经不起折腾。从历史发展眼光去审视,我党取得政权后,采用“阶级斗争”的理论,采用革命斗争的手段,去治理国家,去管理社会,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且已被我党认识并放弃。是年,父亲曾告诫我们:“我百年后,党组织是如何评价,你们不要比人论事,历史自有公论。在后事处理上,不要麻烦党组织和社会,自家追思安葬即可”。并交最后一次党费二万元。
2018年2月春节,我回到湖州,应友人邀请,与儿时邻居陶海燕一同(时任地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陶清女儿),相聚茶叙,并参观飞英公园。该公园毗邻眠佛寺街,是我们儿时玩耍、受害、启蒙之地,故地重游,甚为欢喜也颇多感慨。在韵海楼前,我惊喜看到了红梅,枝干稠密,含苞待放。真是遗憾!没有看到红梅傲霜斗雪,花艳盛开美景。红梅既是西南植物,又含有红色意义,与我人生经历,有诸多人文情怀,故极为钟爱。不管如何,父亲崇尚铮铮铁骨“红梅”的坚贞气节,一直影响着他走过人生艰难曲折的道路,使其思想为之开朗乐观,对人与事能举重若轻;使其意志为之刚正铁骨,坚持党的事业不动摇;也使其能为之长寿至98高龄,受到社会的尊敬和赞誉。这不仅仅是体现一种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也是我们后代需要永记的风范。
二、革命志坚、忠贞尚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父亲在上海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同年8月13日,日本把战火又烧到上海。难忘的11月11日那天,敌机轰炸十六铺码头一带,顿时,祖父家变成废墟,烧光了赖以生存的家业。
父亲回忆说,祖父叫陈宝发,当年家住复兴东路168号,毗邻城隍庙。宅屋临街,店面宽约10米,楼高二层,屋深4进。祖父家业为“前店后坊”,前店做货物买卖,后坊为榨油场所,前楼房自家住用,后楼专供人客宿。然而,所幸家毁人未亡,一家三人逃难回慈溪观海卫,先借宿父亲姑姑家,后租下上横街15号老宅。
祖父迫于生计,租下海涂滩地,春时种下棉花。父亲跟着学干农活,却被本族保长看上,视其有文化,能书一手好字。族长正需一助手,当即委任父亲为副保长。实际是“师爷活”,帮助抄抄写写,但有些经济收入。祖父曾想岀资,让父亲学做生意,在镇上开个店,或者做单帮,跑上海营生。显然,父亲对这些不感兴趣。
忧心国事
父亲以难民身份回到家乡,心里怀着国恨家仇。虽不喜欢这个副保长“头衔”,但在镇上却有了活动空间,时常与进歩青年一起,参加当地抗日救亡宣传。那年父亲仅18岁,年纪轻轻的,忧心起国家命运,热衷起国家事情,经常去锦堂师范附设民众教育馆,在那里看书看报,阅读进步报刊,寻找起民族救亡的答案。正在此时,先后遇到革命思想启蒙导师——时任馆干事的邵明(曾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和朱兆祺(后更名朱洪山),给予经国济世的理想信念引导,使父亲有了新的视野,去寻找改变民族命运的新道路。
父亲8岁那年,在上海家门口,看到周恩来组织的工人武装,与军阀政府的军警激烈战斗,结果工人胜利了。没多久,父亲又看到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老百姓以为可安居乐业,市民们很高兴,举行绕老城厢游行,真的普天同庆。可同年4月,蒋介石指挥了反革命政变,父亲又看到武装军警押解着一串串工人和共产党人,在家门口走过,后来听说被枪杀。是年父亲13岁,又亲眼目睹了日寇侵略上海“一·二八”事变,淞沪战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爱国学生举行街头演讲,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并号召抵制日货。历史也说明,弱国无外交,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与日本签订卖国“停战协定”。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软弱到何等地步,让国人感到何等的痛心、何等的耻辱。那年,父亲虽年幼,但国家贫弱至极,遭受几度侵略,从小激起了忧国图强的心。
然而,父亲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质疑起当时政府治国方略,这些都源于从小激发岀来的民族救亡思想。在与朱兆祺接触中,父亲开阔了视野,渐渐地被“赤化”,接受了他们言传身教的理论。父亲生前回忆,是年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其中的话:“战争的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有深切体会:在近百年中华文明历史中,中国已经“器皿不如人,体制不如人,文化不如人”,要想强国富民,就要走民族救亡的道路。那么,谁能解决中国进入近代化呢?谁又能让中国赶上西洋人呢?中国当下必须在战场上(抗日)取得胜利,这不是政党之争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有支撑战场胜利的力量。这种民众的伟大力量,是需要用民族救亡的思想,有一大批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者,来唤起全中华民众的,并为此而奋斗。于是,在1938年8月,父亲被身为中共党员的朱兆祺看中,介绍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11月,父亲参加慈溪县政府组织的战时服务大队,先任中队班长,后调大队部工作。进而,父亲又参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且认同了以革命方式走民族复兴之路。为此,与有志者结为同志,誓死浴血奋斗,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
尚勇救亡
那时,我祖父家在观海卫镇上横街、下营街一带,这曾是抗倭驻军兵营所在地,属宁波三北地区,是明朝东南名卫。该镇的百姓,大多数系明初卫所屯兵的后代。民间有尚武、习武、勇武的民俗风气。据专门研究观海卫镇历史的莫非先生介绍,卫所内陈氏系望族,在《溪上遗集录录》第二辑有记载,陈克成,福建人,洪武初年,以偏禆随将攻金陵,采石之战殒职。其子邦安率弟邦宁,以步校战陈友谅,取鄱阳、安陆、襄阳等地官洊升指挥。洪武十二年,陈邦宁遂袭其兄指挥职,随汤和来驻卫城,且为观海卫陈氏之始。陈氏后人在近代,有开绸缎庄的、有当地主或财主的,可谓富甲一方。是年,父亲曾回忆,陈氏族长陈宝珊专程来上海募集资金,祖父为修缮宗祠及家乡办学,还捐了不少银两。祖母孙雅娟,祖上也是明代将门之后。据莫非先生研究,嘉靖年间,孙氏先辈叫孙荣,曾任观海卫指挥使,多次率部迎战犯卫倭寇,且观海卫民众见其丰功善政,特立有“善政碑记”。父亲的外公叫孙阿褔,传承祖上“左手棍”武艺,是浙东三北地区民间武林高手。左手棍系少林阴手棍,由南少林传入观海卫,在明朝抗倭时,亦与杨家枪并称为“杨枪孙棍”,驰名江南。据父亲回忆,外公个头不高,有一身武艺,家藏多种兵器,常耍刀弄枪,教人习武练功,称得上大名鼎鼎,方圆数镇无人不知。父亲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会几手,有护身之功。
抗战初期,慈溪县章驹县长受国民党左派、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影响,决定学习上海组建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做法,在慈北、慈东、慈南成立了三个战时服务大队。父亲所在慈北大队,邵明和朱兆祺为正、副大队长,均为共产党人。因此,这支武装大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年,父亲所在大队,动员工作有力,民众抗日热情高涨,青年以踊跃参加为荣,在东山头和观海卫一带做得风生水起,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
据中共慈溪市党史资料反映,当时,全县先后有1000多青年人参加救亡运动,不仅为后来开辟三北抗日革命根据地打下扎实基础,而且许多当年青年人,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中流砥柱,可惜朱兆祺同志却没有看到革命胜利。据党史资料显示,1945年9月,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时,整个四明地区留下地级特派员2名,县级正副特派员11名,朱兆祺与父亲一起受命坚持斗争,朱被任命留守处主任,父被任命余上县委特派员,不幸朱于1946年12月31日牺牲在鄞西潘岙村。1951年,父亲在慈溪县担任领导,朱的妹妹朱虹找到父亲,要求为其兄墓葬。父亲为弘扬革命精神,即安排县民政科办理,朱兆于祺1952年初安葬在依山傍水的慈湖畔。1998年墓地扩建为“慈湖革命烈士陵园”,迁移安葬了一百多名不同时期的革命烈士,并供人们凭吊纪念。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浙东抗日形势急剧恶化,父亲在观海卫党内战友,多人先后被国民党慈溪县国民兵团杀害。同年4月23日日寇占领观海卫及三北地区。5月10日中共浦东工委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南渡杭州湾,登陆三北。于6月18日首战相公殿告捷,日军死伤各8人,增加了浙东民众抗日信心,并于8月在三北成立五支四大总办事处。父亲由此隐姓埋名,对外称去上海经商,实为以革命者的公开身份,从事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到1951年初,先后长达十年,始终没回过家,有时路过家门也不敢入,怕敌人伤害祖父母及街坊。
家国情怀
抗战时,浙东这块根据地面积狭小,孤悬在敌后,时常面临敌伪顽的包围夹击态势,随时有生命危险;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于1946年12月,辞别一起隐蔽在上海的虞鸣菲,回到浙东后,次年4月受命山心县委书记,亦参加1947年5月15日浙东“草茅庵建军”,并任中队教导员。当时,新建武装部队只有43人,分两个排,有1挺捷克式轻机枪,20多支步枪,却遭受浙东5万国民党部队围剿。期间这支弱小的革命武装力量,出生入死,先后突破围堵于姚江,与敌周旋于四明,出生入死于浙东。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虽溃不成军,但残余势力还在,土匪武装还很猖獗。此间,父亲虽没过回家,但仍然思念着祖父母,时常有机会时,拾些柴火或砍些树枝,乘夜深人静,赶上数十里地,放于家门口。次日凌晨,奶奶看到柴火,知道儿子还活着。
祖父母早年在沪经商时,生父亲一独子,视其为掌上明珠,倍加呵护。沪上一起战事,奶奶总会把父亲送回娘家寄养,生怕有失。1950年初,奶奶听邻居说,你儿子回来,在县里工作。奶奶近10年未见,自然思儿心切,就独自找去相见。然而,一心位于工作的父亲还不领情,一见就责怪,您怎么来了?为此,奶奶到年迈时,仍旧唠叨着这个“心结。”当我问起父亲时,父亲说:“刚解放时,工作非常忙,另外,虽夺取了政权,但敌人还存在,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社会依旧有险情。一旦敌方知道母子关系,恐有被加害生命危险。”据长兄说,观海卫老宅邻居告诉他,父亲一直到剿匪形势好转,1951年春夏时,才回家看望过祖父母。当时,父亲仅带一警卫员(当时县委书记外岀,带警卫一个班),只逗留半小时,就马上离开,怕打扰街坊邻居。
自古忠孝虽不能两全,但父亲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为自已“认准的主义”而奋斗,四处奔走,居无定所,枪林弹雨,历经艰险。终于,在浙东区临委领导下,父亲与战友们迎来了全国解放。据有关党史资料显示,在浙东解放前夕,经过几年浴血奋战,浙东部队已发展到6300多人,轻重机枪103挺,已控制浙东大多数乡镇,且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不过,父亲忘我工作又兼顾家庭的亲情,体现了一位革命者的家国情怀。
三、红色恋情,耄耋怀念
2017年清明,我回乡祭祀父亲后,到毗山养老院,去看望母亲。父亲逝世后,母亲一直很悲伤,经常独自暗暗流泪。我见母亲正躺在床上,鼻子插着吸氧管,情绪却平静。母亲见我来了,脸上露岀笑容,想坐起身,我赶紧过去,让母亲仍躺着,拉过櫈子,倚床坐下。
母亲躺在病榻上,回忆起父亲一生,平和地对我说:“你父是幸运的,抗日时没战死,解放前没被捕,‘反右\\\\\’时没受牵连,‘文革\\\\\’中没自杀。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比起牺牲战友来,却幸运多了。不仅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些工作,还能活到98岁,我们应该知足了。”母亲又缓和地说:“你父亲在结婚前,对我说过,北撤至上海时,曾有过一位女友,是上海纺织女工,竭力帮助过他,后来不幸牺牲了。”
沪上探访
父亲撤至上海经历,曾关系到父亲生死攸关。父亲这段红色恋情,给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又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父亲自己不便提及,自然我也就不知情了。这时,我不加思索地对母亲说:“那是父亲生命中,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谁帮助过父亲,理应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们也不能忘了人家。”而当我追问时,母亲就讲不清楚了。父亲性格内向,平时言语不多,但对人十分诚恳。父亲未说此事,自有其道理。母亲随军北撤苏北,历经了战场磨炼,能理解那种生死相依,不会去深究。
父亲离休后,居住在嘉兴,由我大姐项赤兵夫妻照顾着,安逸而平静地度过晚年。但对于上海,父亲仍然情有独钟,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故居,拜会老战友。后来,父亲年事高了,人显得有些木讷,歩履有些蹒跚,很少向子女提出要求。那年父亲已96岁髙龄,自知身体每况愈下,又提岀想去上海,弟弟项泳夫妻即满口答应。然因父亲年事已高,购高铁票时,引起售票员质疑,费尽口舌,总算购得车票。在2014年9月8日上车时,虽有拐杖或轮椅,父亲歩履缓慢,,行动还是显得不协调。最终,在弟弟夫妻和列车员通力配合下,待父亲迈进列车,车即启动。
在上海,父亲很高兴,见到了1946年“北撤”沪上的战友们。有原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江震叔叔及夫人吴紫枫阿姨、原上海国棉14厂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虞鸣非阿姨、及徐冬意(徐英小名)妹妹徐福英等。在虞鸣非阿姨设宴餐叙中,虞仿佛想起那年在通北路“徐元丰面店”的情景,她认真地对父亲说:“你不能忘记她啊!”父亲深有感触地说:“不会忘记的。”然后,她继续说:“那么你给儿子讲过了没有?”父亲略有所思地回答:“还没有么!”此时,鸣非阿姨转过身来,对我弟说:“你父在上海时,有位战友阿姨帮助过你爸,你们可不能忘记她啊!”弟虽感到惊讶也不知由来,但仍然爽快地应诺下来。
回湖州后,父亲似乎感到人生可以释怀了!情感世界可以安然放下了!然而,仍然保持着寡言少语,也未提及那个人生“故事”。时过1年多,父亲就在湖州毗山养老院安祥地逝世。
鸣非阿姨所说那位阿姨是谁?父亲为何至死对其难以忘怀呢!经母亲提起,我想有必要去弄清楚,或许对父亲是一种更好的怀念,或许能兑现我弟弟的承诺。于是,在2017年4月11日,我专程到上海,在南京西路西式住宅里,见到了97岁高龄的鸣非阿姨。她身体健康,记忆清晰,向我娓娓讲述那段父亲经历。不久,我又到上海,见到徐英阿姨妹妹福英,详细了解有关史料。
据鸣非阿姨介绍,徐英生于1922年,祖籍慈溪观海卫人,少年在沪当纺织童工。1937年8月,日本侵略上海,徐随父逃难回家乡。次年,徐参加慈北战时服务大队救亡运动,后因生活所迫,又随父回上海,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活动。于1946年参加共产党,担任毛绒厂党小组长。期间,帮助浙东“北撤”到上海的同志隐蔽斗争。1947年到四明山任姚南白龙潭交通站长,同年9月因叛徒出卖就义。
革命恋情
虞鸣非是慈溪观海卫古窑浦人,家境殷实富裕,在当地称得上望族。其从小送私塾读书,后进新式学堂读书,虽只有四年级,但已是当地第一个进过学堂的姑娘。1941年7月,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到了古窑浦,并成立办事处,有位女干部徐卫平(曾任上海铁路医院党委副书记)住进鸣非家里。在徐影响下,她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且投身到抗日根据地斗争。1944年7月,她在东埠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她因病到上海隐蔽,从事地下工作。此间,经党组织介绍,她认识同乡徐英。当徐英得知,鸣非刚来上海,人地生疏,需解决住宿时,由徐安排在同厂结拜姐妹家,借宿于通北路徐元丰面店楼上。店主叫徐少春,是徐英小姐妺的丈夫。小俩口挤在一楼,腾岀楼上房间,让给鸣非住下。
1946年3至4月一天,徐英阿姨约虞鸣非同行,说看望一位从三北撤到上海的同志。她俩结伴过黄浦江,找到浦东杨思桥,寻到几间茅草屋。徐按地址推开门,走进一间房,看到四壁皆空,仅置有一床,床上坐着你父亲。徐英见了你父亲,就热情地叫一声:“杏根哥。”据虞回忆说:“在我看来,徐英与你父亲是很熟悉的,交谈很亲切。当时,你父亲坐在床上,面容憔悴,还穿着破棉袄,脚上没祙子,光脚穿着鞋子。面临生活无着,亦危机四伏。但你父亲很平静,没提帮助什么。”然而,徐英倒是关切地对鸣非说:“这里怎么能生活呢!我去想办法。”交谈中,徐英有时用闽南“燕语”说话,自然虞阿姨是听不懂的,但父亲依旧没说什么。她俩就此一见,便回浦西。
其实,父亲撤到上海,住在浦东伯父家。父亲伯父叫陈宝明,我儿时在观海卫奶奶家见过,我称其为“大公公。”据父亲说,祖父兄弟俩感情甚好,早年父亲的伯父,先上湖州轧村做榨油生意,后到上海提蓝桥开起清油店,随邀祖父到沪上学业。祖父勤奋好学,也会待人处事,不久自立门户,在毗邻城隍庙的复兴东路开一家清油作坊。那是前店后坊,且雇佣7至8人,加工半成品清榨油。不是工业时代,作坊生意尚可,后期转型做些食品油代理,因此家境还算殷实。日寇侵略上海后,家业被毁,逃难回老家种地。稍后,祖父兄弟俩又合计,长兄再闯沪上,弟坚持种地。但时过境迁,父亲的伯父在沪,亦农亦商,创业难再辉煌,却让父亲有了歇脚之地。解放后,父亲一直感恩当年沪上的帮助,在父亲伯父晩年时,始终给予生活上资助,直至养老送终。
1945年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指示,浙东游击纵队,除少数精干武装隐蔽以外,7天内须全部撤离浙东……父亲仓促受命,带武装队伍在余上地区坚持斗争。当时,中共余上县范围,有余姚5个和上虞2个乡镇区域,基本属平原地区,少许山地。确定坚持斗争的原则,是“依靠群众,依托山地,保存力量,做到无声无息,等待时机。”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一则留下武装人员有20多人,是临时凑配的,与父亲相互不熟悉;二则父亲不是当地人,口音有差异,在白区没有亲朋好友社会根基。且国民党第32集团军两个军先后抵进,还有地方浙江保安团到达,一夜间,整个根据地变了天。
在此情况下,不但没有后勤保障,且一支武装队伍活动在乡村,行动目标太大,不利隐蔽斗争。于是,在父亲主持下县委决定:“动员中型遣散,投亲靠友,待机归队。”不曾想到,两名武工队员回家后,即向国民党乡保长告发我浙东游击队留下人员行迹,并岀卖枪弹埋藏地。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四处派岀特务侦查,亦组织村民联保,布下天罗地网。父亲他们有所觉察后,于是被迫离开,转移到比较灰色地带活动。有一天,父亲队伍在横河乡的小古岭山岙,找到一户独立群众关系,是十多天首次住到群众家里。由于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在这一带,父亲所带武装遭到村民叩门拒开,不愿借宿;更有甚者,鸣锣驱赶,联防围剿。敌人大兵压境,我方力量悬殊,又处平原地带,没有山林隐蔽,形势非常严峻。更为要命的,班长孙启耀和一名战士,本应该守护父亲,紧随一起战斗,但遇到敌情,却自径沿路跑了。此后父亲独自一人,白天躲歩哨、避敌兵,天黑暂息田畈、露宿草堆,所幸辗转跳岀了敌围。父亲与他的战友们,虽坚持斗争近两月,但困难局面一时无法打开,最终决定,父亲暂时撤往上海。
杏根是我父亲家里称呼的小名。父亲青少年时,与徐英阿姨是同乡,同属卫所移民后裔。在沪上亦是隔壁邻居,俩家过往密切,彼此相当熟悉。父亲为陈家独子,家境殷实,培养读书成才;徐英为徐家长女,家境清寒,从小当童工,赚钱贴补家用。俩人虽有不同家境,不同人生,毕竟是青涩年华,又有憧憬未来梦想,故交往甚密。尤其是徐英阿姨性格外向,勤劳聪慧,为人贤恵,助母理家,还会女红,着实令长者所赞赏。在我记忆中,我奶奶作为街坊邻居,看着徐英成长,或许知道徐英帮助过父亲缘故吧!奶奶始终忘不了她,时常在我兄妹前称赞她。日寇侵略上海后,俩家都逃难回乡,时年徐英15岁。受父亲抗日救亡思想的影响,她结识了女共产党朱昭,参加了观海卫民众教育馆创办的妇女识字班学习,加入战时服务大队,参与组织鼓励妇女劳军等活动,由此激发起徐的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同时,使其认识到有文化的重要性,从此始终坚持边做工边上夜校,攻读起会计专业。
1939年春天,徐英迫于生活,随父重返上海,进英国人建的毛绒厂做工。此间,徐英团结工友,助人为乐,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工友义务夜校学习。1941年6月,慈北区委委员沈一飞被慈溪县国民兵团杀害,其妹沈洪沫随父亲到上海,找到同乡徐英。徐阿姨把她当作亲妹妺,安慰她、照顾她,帮她找工作。介绍到自己厂里,学做羊毛衫绣花,并同睡一床,使她在徐英身上得到亲姐姐一样的温暖,助其度过难关。由此可见,徐英在家乡的经历,为其奠定了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徐英阿姨把父亲接到浦西,仍旧安排在徐元丰面店楼上,且为父亲添做全部衣裤,还提供日常开支。在此期间,父亲经常参加工友聚会,也认识了10多位进步青年,其中包括江震、徐怀英(徐英大妹,曾任鄞县妇联主任)、徐少春夫妻。1946年6月,上海爆发了“六·二三”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徐英等工友按组织要求,明知有生命危险,也积极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斗争中去。差不多同时期,由就读夜校教师、地下党支部书记沈一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担任工厂的党小组长。此时,政治活动颇多,面店进岀人员过密,虞鸣非与父亲商量,这里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还是北上找部队。于是同年7月,找到一位熟悉北上路线的带路人,父亲与虞同行前往杨州,拟转往苏北。临别时,徐英送至车站,拿出二枚金戒指,交给虞鸣非说:“到了苏北部队,把戒指给杏根哥,让其作应急使用。”到了杨州,适遇战事,聚集众多国民党部队,父亲他俩焦急等了三天,实在无望,无奈返沪。
回沪后,鸣非阿姨归还戒指,另择住处,找了一个包香烟的工作,隐蔽做工。父亲感到住地达不到“无声无息”的要求,就启用徐英党组织路线,曾找过中共华东局联络部负责人卢涛同志,要求帮助联系北上,他答应可走救济总署船只去苏北,但须耐心等待。父亲久等不及,只好冒险启用浙东组织关系,写信联系上寿静涛(中共余上县委副特派员)。寿正好在上海,父亲按地址找到天潼路钱田庄寿的住处。事后寿又到通北路面店,回访父亲及朋友们。这样,经寿请示浙东领导后,又返回上海,传达让父亲回浙东。1946年12月,徐英再次做了一套冬季棉衣裤,织了一件毛线衣,与江震一同资助现金,并送別于火车站。在时隔一年后接上了组织联系,并与寿静涛一同返浙东,父亲格外地高兴。
2006年11月,我接父母到杭州萧山家里少住,家宅窗台直面官河,父亲望着官河,想起那段战斗岁月,真是感概万分。官河虽不宽,往北连西兴镇,向东通宁波,汇接甬江入海口,是一条连接杭甬的运河。现在,人们已感觉不到昔日的辉煌,当时可算得上是浙东的黄金水道。
次日一早,父亲独自柱杖歩行,寻到当年西兴码头。回家后,父亲仍兴致盎然地对我说:“当年,西兴码头繁荣,河道有舨船、客货船只等,岸上有客栈民宿,街市商贾,日人流数可达一至二千。从上海回宁波,坐火车到杭州,再由西兴坐船,须用1.2至1.5银元,卧席均加40%左右,一般乘坐23小时,方可到达曹娥码头。”曹娥码头是浙东水运交通枢纽,这里连接余姚和慈溪两大水网地带,走余姚去慈溪各地,均在此分流前往。
然而,父亲多次往返,选择乘夜间航班,求得平稳速快,夕发早至,船价划算。上岸后,父亲跟随寿静涛乘脚划船至临山秘密交通站,而后又到八字桥联络点,再歩行上四明山,见到了时任中共四明工委副书记的陈布衣、朱之光开始投入新的战斗。后来,父亲受命中共浙东区党委海上工作委员会书记,联络浦东地下党与苏北中共华中工委时,仍选择过走西兴这条水路。
慷慨就义
1947年3月7日,中共华东局卢涛同志(系南京雨花台烈士)、徐英的直接联系人沈一民相继被捕。沈在狱中托人传岀暗语口信,要求她们迅速转移。这时,徐英找到鸣非阿姨商量,鸣非明确说:“项耿已回浙东,那里正需要人,我们还是去四明山。”这样,经组织同意,徐英阿姨冒着被捕危险,她挨个通知所有其联系的党员,并安排鸣非等数人先隐蔽或撤离上海后,才在是年3月19日,带领江震、徐勇、徐怀英撤往浙东。到了浙东,接受组织审查后,鸣非阿姨先后任余姚左溪乡支部书记、大岚区长;江震参加了“茅草庵建军”,为武装部队机枪手;徐英任浙东姚南地区白龙潭交通站站长,同年8月10日因叛徒岀卖被捕,次月11日慷慨就义,时年仅25岁。解放后,将徐英被捕村,命名为徐英大队(村),以志纪念。
听了鸣非阿姨讲述后,我想前往徐英村去实地考察,加深对英雄事迹的感悟。2017年5月3日,我约了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宣讲团康小平团长,俩人乘坐高铁到余姚,在鄞州区工商联副主席励佩珍夫妻驾车帮助下,由梨洲街道副主任陈杰派人陪同,找到了上王岗村的党支部书记黄远文。据黄书记介绍,该村辖有6个自然村,有800多户人家,是四明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地带之一,也是连接奉化、鄞州、余姚三地的战略要地。解放战争时,这里回旋余地大,进可去三北,退可走鄞西,故在此打过几仗。当年,中共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时常隐蔽或运动在这一带,徐英就是在我村被浙保团碰上被捕的。
我们在村干部陪同下,前往徐英当年被捕地一一阿秋嫂家。那是一片竹海,越山涧,过石挢,走石路,爬坡坎。我们走入深山竹海,两侧高大竹林,密得不见底,把路上天空都遮住了,没有当地人带路,恐怕很快就会迷途。可以想象,当年父亲那帮革命的“土地菩萨”们,在这块山地上,学会了游击生活,会跑远路,会爬高山,会钻密林,且拿起柴刀,会建茅棚,筑起了一座无形的红色堡垒。在父亲撰著的《战斗的岁月》回忆录中描述,为不打扰山民,他们自建“公馆”,篾席盖顶,竹爿编床,皓月当灯,竹声当歌。晴天闲坐在石块上,或操练在坪坝上;雨天盘坐在竹床上,漫谈闲聊,看书阅文,练字下棋,虽物质生活艰辛,但大家团结友爱,精神生活颇为丰富。
不过,父亲曾对我说:“冬季来临,山林里很寒冷,生活更为艰难,常会缺衣少食。这时,黄连叔叔(虞鸣非丈夫,时任中共山心县委副书记,原上海市经委干部考察办公室副主任兼委机关支部书记)是当地人,就生存能力来说,比外来同志更能发挥作用。他不光地形人头熟,而且点子办法多,他带人下山一趟,就能借到所需战时布匹和粮食。”
约走20分钟路程,来到阿秋嫂住家原址,房屋建筑已没有了,搬往大路边。但是站在那里,依稀可分辨岀,当时隐蔽在竹林中那很不显眼的民宅地基。我仔细观察,是坐北朝南,依托山坡,顺着山势,坐落有块坪坝。宅坝前面山势陡峭,坝坎用石块垒起,坝前下方有一口井,四周便是竹林遮蔽。如果不是当地人,根本想不到这里曾住过人家。据介绍,在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时,阿秋嫂夫妻是拥护共产党的,他家曾经是部队的被服加工地。在当地,我们见到阿秋嫂后代,他讲述了徐英被捕遇难经过、以及他家情境。使我感受到,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老区人民,没有忘记为新中国建立而作岀贡献的山区群众,也包括阿秋嫂。
据鸣非阿姨向我讲述,薛驹(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经上海来到浙东,他知道华东局情况变故,证明了鸣非和徐英俩党员身份,并恢复党组织关系。那天,鸣非阿姨很高兴,与中共梁弄区委书记梁辉一起,想把这消息告诉徐英。当走到白龙潭时,遇见一小男孩,说刚才浙保部队,将一位上海人女共产党抓走了,你们不可再往前走。他俩立即返回,了解情况,设法营救。
是年,父亲所在部队从三北撤往四明,韩茂洪排长(曾任余姚县民政局长)率部队突围姚江时,有三位战士负伤,原本不属徐英阿姨工作,但其主动帮助护理。又因山里没东西吃,于是,徐想到阿秋嫂处买些米和鸡蛋,给他们补养身体。不巧,叛徒带敌人来到阿秋嫂家,且指认徐英是共产党。徐英为保护阿秋嫂夫妻,大义凛然地对敌人说:“我是共产党,你们要抓就抓我好了,与他们无关。”此时,阿秋乘敌不注意,跳下坝坎,躲进密林。徐英和阿秋嫂在押解往梁弄路上,徐英一直告诫阿秋嫂:“不要害怕,一切往我身上推,说是我们用枪胁迫的,你们是岀于无奈。”不久,阿秋嫂被释放了。
敌人以为抓到女共党,可供岀四明地区领导人住处或部队行踪。然徐英阿姨却坚贞不屈,毫不泄露,于是敌人用尽种种酷刑逼供。据鸣非阿姨回忆说:“徐英吃尽了苦啊!敌人用石板压在她身上,用竹签扎进她手指,用铁钳拔掉她脚甲等等酷刑……”用刑受虐长达一个月,实在榨不出什么,与那个叛徒一同被推上刑场。在就义前,徐英对叛徒蔑视地说:“你吃不了酷刑,而告发了我,最终落得与我一样。不过,我挺过来了,但我的鲜血,不能与你流在一处。”说完后,拖着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身躯,毅然艰难移向另处,并面向国民党反动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永垂不朽
徐英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同时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人,有着崇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那就是为了主义而“年纪轻轻闹革命,年纪轻轻去断头。”为此,也更加激励了革命者,为民族救亡,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勇往向前。在部队宿营集合时,当父亲宣布徐英牺牲消息时,据江震回忆,父亲热泪盈眶,讲到情感深处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鸣非阿姨痛恨不已,誓言为死难者复仇。在她领导的区乡,组织了“复仇队”,并任副指导员。虽该队不久并入主力部队,鸣非也调任大岚区当区委副书记兼区长、武工队长,依旧双手使枪,能文能武,带领队伍,转战四明,名震大岚。
江震叔叔,在晚年撰写题为《徐英大姐引导我参加革命》文章,曾刊登在宁波日报。文中提到其在上海一所工人夜校,认识了长他6岁的同学徐英。她为人很厚道,待人诚恳,只要同学有难,都能尽力帮助。1943年,江震父亲在江西被日寇飞机炸死,不久母亲因病不幸离世。是年,江震仅14岁,就得到徐英的关心和体贴,使其度过失去父母的痛苦。后来,徐英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江震随徐英上四明山后,先为父亲警卫,后父亲考虑其是工人岀身,又有文化,若在野战部队培养,更能发挥其才,当了机枪手。解放后,部队选拔飞行员,江震已是连级职务,经考试而被录取,成为我国第一代飞行员,也成为浙东武装部队走岀来的一位空军中将。1976年春夏时,我曾到长春,去看望时任空一军军长的江震叔叔,可惜那年江叔叔去援建柬埔寨,而没能聆听到他的教诲。
2014年9月,父亲在上海与江震(左)前往虞鸣非家时合影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徐英阿姨为国献身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浙东人民。同时,浙东人民为缅怀她,在她牺牲的梁弄,为她建了烈士陵墓,以供凭吊纪念。当得知徐英故事后,使我想起了在重庆英雄就义的“江姐”烈士,我们是听着“江姐”革命事迹和唱着《红梅赞》歌声成长起来的,由此更加激起了我对先烈的无比崇敬!
<p sty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