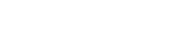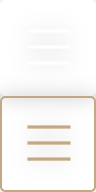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19第06期(总第二十七期)
风雨兼程行色匆 四明山上一布衣(下)
——缅怀敬爱的陈布衣伯伯
文/时雨
4、依依送别“亲人”,那是“把人头掖在裤腰带上”的艰难岁月……
我曾陪同父亲去见陈伯伯。在两人的对话中,我听出他俩对抗战胜利、部队“北撤”后那段时光的缅怀。我看见了陈伯伯脸上落下的眼泪,还有我父亲的呜咽之声。陈伯伯说:“四明山斗争最难熬的时期,是送别‘亲人\\\\\\’后的艰难岁月,那是把人头掖在裤腰带的年代……”他说“我们有好多政治上成熟、革命性很强的同志,就在那时候牺牲的。”
事后我看过陈伯伯的回忆录,觉得在他一生中,部队“北撤”是人生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幕,是一道他在感情防线上永远迈不过去的“坎”。
抗战胜利,这是意料中的事,只不过来得突兀一些。可正当陈伯伯满怀信心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余姚城关时,却接到中共浙东区党委的通知,停止前进撤至陆埠待命。9月上旬,国民党第32集团军3个军的先头部队开抵杭甬线,9月16日,接受驻甬日军的投降。当天,107师进驻宁波城区。18日,123师(预备第三师)进驻余姚城关。22日,最后一批日军赴杭集中……
陈伯伯在回忆录中说:“ 9月23日,我和朱之光同志接到县委书记俞震从上虞丰惠镇开会回来带来‘北撤\\\\\\’命令和区党委的具体部署。宣布已经区党委批准,由县委委员、组织兼宣传部长陈布衣留下,领导和坚持工作。”
陈伯伯说:“当时我和朱之光都感到很突然,不约而同地到丰惠镇去找谭启龙同志。只见他两眼布满了血丝,喉咙沙哑。他疲惫地和我们谈了约40分钟,从国内形势谈到北撤和坚持。关于坚持工作的方针,他说:部队要北撤,但党是不撤退的;我们党的旗帜是要高举的,要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当时我提出要搞武装斗争时,他说:不要你搞武装,只领导秘密党组织。但他同意留下姚南中队和大陆商场(敌工部)的一批武器,归坚持四明斗争的负责人刘清扬安排。南山县委原定朱之光北撤,他是县长,面目较红。但朱见谭启龙时要求留下来。谭同意他留下,并嘱咐要有自卫武装。当我俩回去时,他又指示我们要‘面向群众背靠山,扎根于群众之中\\\\\\’,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
对身处和平环境中的今人来说,浙东新四军“北撤”后,四明山区陷入“白色恐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是无法想象的。据史料记载: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国民党调集正规军两个师,即98军123师(暂编第三师)、124师(暂编第四师),在32集团军副司令陈沛指挥下“拉网式”地推进四明山,进攻目标就是浙东红色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南山县。
据陈伯伯回忆:敌人的“清剿”分为两个阶段,从10月5日到10月底,占据平原区和四明山外围集镇,称为“清剿”阶段,11月初,分路进入四明山腹地,逐村搜捕我党工作人员,称为“清乡”阶段。历时约半个月,又陆续撤回所占领的集镇……
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了发生在194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清乡”行动时我四明山领导机构隐蔽在屏风山的境况,陈伯伯说:“在国民党即将发动‘清乡\\\\\\’时,我最担心的是四明特派员刘清扬的安全,他那儿有电台,手摇马达会发出声音,我特地跑去他的公馆商量转移问题。当时他也在考虑转移,派人到屏风山侦察地形。屏风山东靠奉化,南接嵊县,西通上虞,北连余姚;坐落在四县交界处,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当地群众以烧炭、种玉米为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当下我俩商议停当,就率领17名工作人员从余鲍陈村出发,到南黄‘公馆\\\\\\’站脚,又到马家坪筹集了四五百斤大米和咸菜、盐与炊事用具分挑上山。刘清扬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每行走一步都叫大家用竹棒把草扶直,这样就不留痕迹。这条山路崎岖不平,很难走。我们走了四个多小时,找到一个管毛笋人住的草舍安顿下来……”
陈伯伯说:“我们17个人在山上组成一个队,由刘清扬任队长,我任支部书记。北撤时,留下纵队司令部的通报台和《新浙东日报》的新闻台,因部队从苏北向山东转移,通报台功率小,接不上联络信号,只靠乐子型同志抄录新闻台的新华社明码电讯。组织大家学习,增强斗争的信心。没多久,挑上山的大米吃完了,家住在山脚下的大俞村三位同志,从村里挑了三四担玉米上山,大家用脸盆煮玉米吃。吃到后来,每个人都牙齿酸痛,见到玉米就反胃。玉米吃完后,我发动大家采集野果子充饥,山上不时有野猪、野兔,还有山鸡出没,但我们不能开枪,只好让这些猎物自由自在地出现在眼前。”
“在屏风山上,有件事值得一提:有一股抗日时期曾向我军投诚的土匪,因不愿北撤,此时又重操旧业。在敌人逼迫下,他们也上屏风山避难。为了我们不致腹背受敌,我代表党组织和他们打交道,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直至解放。”陈伯伯又说:“当我们隐蔽在屏风山时,分散四明山区隐蔽的还有:朱洪山带领12个人隐蔽在余姚、鄞县、慈溪三县交界的孔岙村附近的陈岙山露鸡岙,他们在露鸡岙搭了一个茅舍,称为‘林公馆\\\\\\’,直到1946年5月才转移;朱之光带领10余人隐蔽在姚南左溪乡七丘田附近的几个山岗,即七丘田、瑞林岗、培龙岗、六塘岗等。鄞县特派员陈爱中带领12人隐蔽在鄞西山区……”
陈伯伯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一段黑色的岁月,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在这时牺牲了。”由于国民党清剿,我们和三北地区失去了联系,据项耿等同志后来介绍:他们所遭遇的处境比四明山区还要严峻。我们还有约一个月时间‘准备\\\\\\’、且山上容易隐蔽。而他们待部队一走,就完全暴露在白色恐怖之下。”他说:“白色恐怖笼罩三北,如观城淹浦乡民兵大队长、共产党员裘登法惨遭杀害后,被割下首级悬挂在淹浦乡柴家村樟树墩。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等五人,除一人脱险外,余四人全部牺牲。余上县特派员项耿、副特派员肖贻带武工队活动时被敌人冲散,无法开展活动。慈镇、余上原有两支20余人的武装,因处理部队北撤的善后工作不得已埋藏枪支,遣散了人员……”
他说:“只有慈镇县庄市区特派员沈宏康和丈亭区特派员范雪伦以做雇工为掩护,在原地区隐蔽下来,一年后才由鄞慈兼慈镇特派员陈爱中通过陆子奇找到沈宏康同志接上了关系。”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留守在浙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为了把红旗继续打下去,改变这白色恐怖的局面,我们迫切需要得到上级党委的指示。”
陈伯伯简单回忆了他北上寻找党组织的经过:
片断A:1946年6月的一天,我在政治交通李阿福陪同下,约在后半夜两三点钟,从陆埠洪山乡余鲍陈出发,随着出市的群众擎着火把向大隐方向走去。仅在离我起程一个多小时后,敌人就包围了余鲍陈村搜捕我党工作人员。我在大隐穿上了刘清扬送我的一件白细布衬衫,随身带了一些笋干、茶叶,化装成小商人。我俩买了4点钟宁波去上海的轮船票,第二天凌晨就到了上海。我们的行动在上海也只有孙敏儒夫妇和金长谷等个别同志知道。但由于从浦东去苏中的船没有‘落实\\\\\\’,我在上海耽搁了四十多天……
我在上海没有‘身份证\\\\\\’,为了搪塞前来检查的警察,我几乎每隔三四天就换个旅馆,有一次碰上了,我说我是生意人他们不信。后来在上海同志的遮掩下才勉强过关。中途联系上船,因船老大是土匪遭‘洗劫\\\\\\’,亏得上海同志找到大团镇储贵彬(我党隐蔽武装力量负责人)‘担保\\\\\\’总算脱险。
片断B:8月初,我与孙敏儒、郑惠民(政治交通)一起,从川沙乘船去苏北,孙曾在浙东纵队后勤部工作过,北撤后他与“华中海委”有联系。我们三人经东台、兴化,到了淮安;由北辙同志的介绍,才找到华中军区,张鼎丞司令员单独约我谈话。我一见到他眼泪就流下来了,汇报后张司令讲了内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要求我回去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见过张司令后我继续向北走,一路上同样不太平,我走了四天后碰到皮定钧旅的一位团长搭道同行,9月5日才在黄河故道旁的山东临沂找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分局。分别见了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和一纵副政委谭启龙,才算真正地回了“娘家”。
片断C:我从淮安北上山东时,孙敏儒同志即返浦东,按照我的嘱咐回四明山向刘清扬传达了华中分局的指示。1946年9月初,刘清扬召集朱洪山、陈爱中在鄞西十八级岗的“永安宾馆”开会。会议调整陈爱中兼慈镇县特派员,慈南、鄞西统一归朱洪山领导,虞东归南山县管辖由朱之光任特派员。会议的另一项决定是以刘清扬同志亲自主持宁波西郊联络点工作。
片断D:9月29日,我北上归来时带回了华中分局关于浙东工作的指示信。此信的精神与我在淮安时让孙敏儒带回的“口头传达”是一致的,但更加详细、具体。内容主要有有四点:一是发展武装工作队,扩大活动地区,在一切有利的可以发展的地方,到处去发展组织武工队。二是一切为了开展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三是在发动群众武装斗争中,组织群众斗争中发展党。四是争取两面派,做好两面派的工作。从此,四明山武装斗争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五、胜利的红旗由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46年12月4日,朱之光同志领导和组织了“天华缴枪”行动,缴获了城北天华乡公所的机枪一挺,步枪13支、短枪2支,子弹200余发。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四明地区第一次缴枪战斗,也是一次缴枪范例,为我游击纵队草帽庵建军赢得了一批武器装备。陈伯伯说:“当我北上请示返回上海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特别高兴。后来,我们将天华缴枪作为范例,向四明各地推广。”
然而,敌人的杀戮仍在继续。晚年的陈伯伯特别容易动感情,他在回忆朱洪山牺牲的经过时泣不成声:“1947年1月2日,我从《申报》上看到了朱洪山牺牲的消息。当时我正在上海等待上海会议结束,随刘清扬返回四明。我希望这消息是假的,但事实证明他确实牺牲了。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轮流悬挂在陆埠镇和慈城的城墙上,朱洪山是我的老战友,一个革命意志坚定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他有武装斗争经验,也有政治工作实践,他的牺性是党的重大损失。”
“从隐蔽坚持转入武工队活动时,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继朱洪山牺牲之后,1947年春季,余上县特派员黄明,鄞慈县兼慈镇县特派员陈爱中也相继牺牲。”陈伯伯悲痛地说。
在解放战争时期,浙东“草帽庵建军”有着特殊的意义。陈伯伯在回忆录中写道:“它意味着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说:“四明工委首次会议在顾德欢主持下召开的,当时刘清扬已去台属,工委委员只有我与朱之光两人。这次会议时间是1947年5月11日至17日,地点在慈南孔岙村山上的‘公馆\\\\\\’,主要讨论四明山工作的总方针、策略及扩军等问题。”
陈伯伯回忆说。“5月15日晚,我们在慈南余鲍陈村北的草帽庵山上召开建立四明主力武装大会,宣布主力部队番号和班以上干部的名单。我们事先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磋商,主力的番号称作第四中队,辖四个班。其中两个班由经过坚持斗争考验的武工队员组成。一个班由抗日时期当过民兵的贫苦农民组成,另一个班由新入伍的学生和工人组成。共有战斗员43名,武器有轻机枪1挺,步枪43支。班排以上干部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锻炼,政治素质好,有实践经验。”
“四中队建立后,首先出击三北,同时制订了6月份工作计划。以扩军、经济工作、群众工作为中心。恢复根据地群众的斗争热情。同时,建立后方保障工作。工作中心是:情报、交通联系、医药、修械、政治宣传等,使群众感觉到以前的三五支队又回来了。”
“为何挺进三北(镇北、慈北、姚北)?”陈伯伯告诉大家:“相比四明山区,三北地区物资丰富,盛产粮食、棉花和食盐,且人口密度大,文化较普及,是贫瘠的四明山区军需与兵源的供应地。”他说:“部队在三北一直坚持到六月底,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也有十几次,使新生的武装力量经受了考验。但我们的力量毕竟太薄弱,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会,又开始对四明山区发动新一轮的‘围剿\\\\\\’。四明工委在分析敌情后认为:“反‘清剿\\\\\\’不是单纯的保存自己的力量,而要主动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在斗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
据余姚党史资料记载:“湖头庙缴枪”和建立第五中队,是继浙东四中队成立和挺进三北后又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
湖头庙位于姚南沿江区凤亭乡,国民党余姚县警察局在此设立分驻所,驻有一个保警中队和乡警卫班,控制着姚南和姚北的要道,为拔掉这颗钉子,朱之光和杨光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他俩发现保警队内有一个队员,在抗日战争时当过民兵,便由杨光与他多次接触教育后,他愿意作为“内应”。于是,在7月19日晚他值班时,姚南武工队根据事先约定信号,在敌人尚在睡梦中时冲进庙内……
这次“行动”共缴获机枪一挺、步枪46支、手榴弹6箱、子弹三四千发;我方人员无一伤亡。7月下旬,以姚南武工队为基础,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入伍,以缴获的武器为装备,在姚南的七丘田村建立了四明地区第二支主力中队,番号为第五中队。这次缴枪在浙东革命史上,与草帽庵建军一样具有重要意义,不但装备了“五中”这支在解放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部队,而且严厉打击了敌人的“清剿”与“扫荡”,动摇了敌人军心,对整个四明山区斗争作出了贡献。这儿有必要说说武器对四明山区革命斗争的作用。当时我军武器非常缺乏,四明山区尤其如此。在1948年 5月中旬,储贵彬伯伯率装备精良、300余人枪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与大团自卫队从浦东南渡上四明山之前,部队的武器来源基本都是靠缴械所得,“湖头庙缴枪”就是范例。
令陈伯伯记忆尤新的是“第三支队”成立,与稍前“袭击临山镇”以及稍后的“马家坪战斗”。直至晚年,他说起这两次战斗仍然眉飞色舞。他说:“第一次去三北后,我就与顾德欢同志商量,如何再次出击,打开姚北、虞北的局面,建立余上根据地。1947年9月初,趁敌集中兵力向姚南、慈南、鄞西地区发动疯狂‘清剿\\\\\\’时,由我带领‘四中\\\\\\’至嵊县和上虞交界的高山地区隐蔽行动,‘五中\\\\\\’坚持在姚南与敌周旋。9月底,‘四中\\\\\\’、‘五中\\\\\\’在鄞西大坪地会合,此时,华中军区派曾在抗战时期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警卫大队大队长的刘发清到四明山区,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根据敌情分析,我们于10月14日晚渡江到达姚北山区,与余上县的同志商量后准备袭击临山镇。16日晚,部队从驻地出发,进至临山镇东门外时,与镇警察所的十余名警察遭遇,经我们射击和猛冲后敌逃窜。我们按照作战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奔袭警所,敌闻枪声迅速溃退,仅毙哨兵一名,缴获步枪一支;另一路冲击镇公所,俘3人,焚毁全部文卷。这次战斗虽缴获不多,但对敌震动很大,敌报刊载:‘苏北共匪大部潜回\\\\\\’,余姚全城戒严,正在集训的自卫队逃跑200余人。隔日(10月17日)晚,部队在姚北四海乡祠堂丘宿营时,突遭浙保一个大队和余姚县保警队三路袭击,我部在刘发清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在敌人距我们只有三四十米时举枪猛射,然后发起攻击,一举击溃敌军。”
陈伯伯补充说:“那次我们离开姚北返回四明山区后,即成立‘第三支队\\\\\\’,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四明山区的一桩大事。随即我率四中、五中和领导机关,搬至山峦起伏、地势险要的姚南马家坪村,准备总结近两个月对敌斗争的经验,想不到又与前来进犯的‘浙保\\\\\\’打了一仗。”
“那时战斗很频繁。我们在强调以军事力量打开局面同时,利用节日和重大事件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和教育活动。1948年初,我与朱之光商量后,在左溪乡长田村召开了四明工委第二次会议。会议中间我们遭受了一次袭击,顺利撤出后继续开会。
据宁波多地党史记载:在陈伯伯和战友们共同努力下,这时四明山地区的武装力量,在敌人组织的三个月“清剿”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定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的主力武装,由四明、会稽两个地区主力武装合编而成,由刘发清为支队长,马青为政委,张任伟为参谋长,诸敏为政治处主任。
这支部队在浙东临委领导下,在短短半年中经历了嵊东协和乡青岩村“青岩战斗”、余姚鹿亭乡的“中村战斗”和姚南“流水潭战斗”、“洪家洋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对浙东工作两次指示精神,和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抓回主动权,实施“战略反攻”和“华野”三个支队率先南渡长江的军事步署。
在众多战斗中,“激战上王岗”令陈伯伯记忆深刻。他在回忆录中说:“5月28日,我和‘临委\\\\\\’领导及三支、五支在东茅山、上王岗、倪何村一线宿营。林枫与临委领导认为:必须给尾随不舍的敌人(浙保安约一个团、四个营)一个‘教训\\\\\\’。凌晨,三支队派出的游击小组与敌人接上火,随即,五支七中、三支‘钢铁\\\\\\’部队抢占上王岗高地,五支八中、三支‘坚强\\\\\\’部队侧翼机动;五支一大在梅岭保卫临委机关,摆开战场……”
“敌人在浙江保安副司令王云沛指挥下,集中了约两千人的主力,形成五道包围圈。战斗十分激烈,从上午8时许开始打响,一直到下午5时许,我当时任支队政委,和张任伟、诸敏等指挥员都到前沿指挥,我们坚守上王岗前沿阵地的三支‘钢铁\\\\\\’、五支七中;连续击退‘浙保\\\\\\’一个团的七次冲锋,敌人的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许,我方弹药所剩不多,我命令采取沉着待机、进行小群近距离反击的战术,双方形成胶着状态。后来发现敌军约一个营在距我约200米的毛竹林集结,准备发起冲锋。我急调集十几挺轻机枪,集中最后的一些弹药迂回到敌侧翼一阵猛扫,使敌当场就死伤几十人溃退……”
陈伯伯说:“这是三支队和五支队并肩作战的一场硬仗,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浙东地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敌我投入兵力最多、伤亡也最大的一次战斗。在战斗中敌人伤亡百余人,俘虏、溃散开小差数百名;我军也牺牲、负伤几十人。但此仗打出了军威,鼓舞了根据地的军心和民心。”
1949年初,面临失败而丧心病狂的敌人作垂死前的挣扎,又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活动。为避开敌主力,留在四明山区的主力五支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依靠群众在山林间与敌周旋。
2月10日,由顾德欢、王起等同志率领的“临委”机关向会稽移动,马青在解放三门和第二次解放天台后,率主力三支队同去会稽与浙东临委机关会合。至此,浙东几个地区联成一片。“临委”为配合大军南下,决定以第三支队为主,更好地组织各分区力量,发起较大的带战役性的对敌进攻。于2月2日、3月3日两次通知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带主力来会稽会合。
陈伯伯回忆说:“我参加‘临委\\\\\\’领导工作后,根据中央指示和‘临委\\\\\\’部署,于4月20日率五支队仍返四明,参加了接受敌‘青救团\\\\\\’起义和扩大开辟根据地、迎接‘南下大军\\\\\\’等一系列工作。直至5月16日,我率五支队在夏巷截击逃敌后与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22军在四明笙竹岭会师。”
六、战友、亲人缅怀陈伯伯,称他为四明山人民的好儿子
(一)、战友的怀念:
朱之光:陈布衣同志那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远大理想与现实斗争目标紧密结合的精神,特别是他经常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始终当作首要任务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陈布衣的最大特点和高尚情操就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无私奉献。他不仅熟读毛泽东著作,也熟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他的名字原来叫裘祖恩,后来他自己改为“陈布衣”,我认为改得好,我理解“布衣”就是“老百姓”,永远是老百姓。这也是自我约束与自我修养。因此,后来不少人叫他“布衣书记”。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受到大家的赞扬。解放后,我们宁波地专机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开始,有人认为:“四明山山高虎大虎多”。三反结束,我们四明山(干部)不仅没有“大老虎”,连“小老虎”一只也没有。这与陈布衣同志的领导以身作则、处处廉洁奉公有关。
陈布衣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遇事与群众商量,关心民间疾苦等优良作风,人人称赞。他不仅在战争年代如此,解放后在宁波地专机关也如此。他长期住在月湖畔那座老旧的平屋里,人在宁波城里,心往往还关心着四明山老区人民的生活。在他的家里,老区来的“客人”特别多,他总是同他们面对面谈心,一日三餐,热情招待。有的家庭困难的还要送给他回去的车旅费、棉布、肥皂等。
江震、肖强:陈布衣同志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当时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是一位老革命和老首长了。可是他丝毫没有摆出自己的老资格或居功自傲的架子,穿着方面与山里的普通老百姓没两样;他吃的是和我们一样的大锅饭,平时行军走路到宿营地,也没有脱离一般战士的生活。无论是对待战士还是群众,讲话平易近人、深入浅出。就是他,把深奥的革命道理说得人人明白,个个受到教育。他对大家很讲民主,十分注意听从不同意见。对于错误的想法,坚持耐心地说服。在这样的耐心教导和谆谆善诱下,我们游击队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一个团结友好、互帮互学、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的一支战斗队伍。四明山的平民百姓,也成长为积极支援革命队伍的群众。大家普遍反映:“陈布衣为人,处处为我们做出榜样。
杨展大:陈布衣同志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之一,他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他热情关怀同志、教育同志的话语尚在我耳边回响,他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尚在我脑海中印着。我当以老领导陈布衣同志为榜样,保住革命晚节永葆青春,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项耿:陈部长对四明山、浙东革命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为人也令我由衷尊敬。陈部长外表温文尔雅,待人接物谦恭和蔼,内质刚毅。革命责任心极强,执行党的方针任务坚定不移。
乐子型:陈部长不忘革命老区,不忘革命历史的精神令人敬佩。他经常到四明山老区乡村走走,了解民情,访贫问苦,老区人民也忘不了他,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说,有什么困难也要找到他家反映。我几次到他家,几乎都碰到来自四明山的赤脚朋友。他笑着说:我家是老区人民的联络站。过去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支持掩护了我们。现在我们进城了,掌权了,怎么可以忘了他们呢?我工资高一点儿,他们有困难,我招待他们吃饭、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是应该的,心里也就好受一些。
胡志实:他无私无欲、废寝忘食,辛勤工作,为四明乃至浙东地区的解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温文尔雅有谦谦君子之风,更有军人的刚毅和胆略,在危难时刻,他总是昂首挺身站在部队最前列,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他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其英名响彻四明大地,谁人不晓?他品德高尚,高山仰止。
杨光:我有幸参加我党在1945年春天举办的四明党训班,亲身聆听过陈布衣同志的教育。在梁弄章雅山的一座大房子里,我们听了县委书记俞震“关于党的基础知识”和县委组织部长陈布衣同志“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报告,令人印象深刻。这次党训班,最后由区工委组织委员黄明(金达)领着我们十几位新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入党。
……我在离休(1980年11月)后,专程去宁波看望老领导陈布衣。陈布衣同志谈了自己关心四明山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问题,说我们老同志不能进了城市忘了老区的人民,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他还对我说:过去我们忙工作,不管家务可以原谅,现在离休了应该当个“家庭政委”,家里的大事还要管,对子女进行教育。按照陈布衣同志指点,我真的当上了“家庭政委”,全家年年评上“五好家庭”,西湖区灵隐街道还叫我作“怎样当好家庭政委”的介绍,《浙江日报》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林言凡: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我随陈布衣同志去镇海参加党史座谈会,他遇到陆子奇同志,突然问她:“老赵好吗?”大家都愕然,他也意识到说漏了。陆子奇的爱人赵士炘在“文革”初辞世已多年了。赵士炘是布衣同志北上时向浙东纵队老首长要来的干部,他特别怀念他们。他很赏识赵士炘,初到四明,就安排他到慈镇县当第一把手。解放初,他向顾德欢推荐,把赵士炘调到公安部门搞肃特工作。
他在晚年常常怀念老战友,尤其是牺牲的战友,他说:上王岗战斗时我们牺牲了12名同志。解放前夕敌人还把我们4位被捕的同志活埋在中村的毛竹山上。他说我恍惚又见到了一幕幕情景,耳际又响起那时的追悼歌:“安息吧,牺牲的同志,你的血照亮了路,别再为人民担忧。”
(二)亲属的怀念:
刘浩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来到布衣身边,携手相随近30年,相濡以沫。深感他不仅是我的丈夫,还是我敬仰的老师,他乐观,总是向前看,不论在哪种环境中,对信仰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从不动摇,他体现着许多党的优良的传统,人性的美。最闪亮的是他一生与劳苦群众几乎溶为一体的至诚关系。
我曾问他:“你为什么改名为布衣?”他说:“那时候参加革命,不改名换姓一经查出全家就遭殃,几乎所有人都改名字。我想了很久才取了这两个字,布衣就是老百姓,革命也是为了老百姓,还可以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可以忘记这个本,忘记自己同群众是同一个命运。”
在病床旁,我曾问过老陈:“百年后,你是回老家嵊县还是留在宁波?”他说:“我很留恋宁波,从1942年组织调我到余姚一直没离开过,她是我的第二故乡;特别是四明山的老百姓。我们之间有感情,把我埋在那里吧,让我永远和四明山的父老兄弟在一起。”
陈鲁滨:我经常问自己,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对我们子女来说这么熟悉、这么亲切。他经常说自己是个普通的人,我们认为他确实是个普通的、却是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忠诚于党。
“文革”时父亲被隔离审查,他关押时有一个班的解放军看着他。妈妈和我都非常挂念他,不知他在里面怎么样?有一次造反派押着他回来抄家,爸爸见到我妹妹小滨时交给她一支钢笔,非常随意地说:“给我灌点墨水”。小滨一下子就明白了,她接过笔趁人不注意跑到月湖边打开笔套,果然里边卷着爸爸写的一张纸条:“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不要担心。”他是想让我们放心,他不会放弃,他会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当时妈妈也在受审查,这张纸条带给她和我们巨大的鼓舞。
对我们子女来说:父亲是个严父也是个慈父。他爱孩子但从不娇惯。记得上初一时我与同班同学一起下乡劳动了28天,回家时两条腿都是蚂蝗咬蚊子叮留下的伤口,还流着脓。我很委屈地指给父母看,父亲却说:“这些抹点紫药水很快好了,你不过劳动了28天,想想农民伯伯他们可是一年到头在地里劳作的,比你辛苦多了。”
他从来不打骂孩子,从来不疾言厉色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他的教育方法是鼓励、引导,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自己去作结论,自己去决定怎么办?所以我们这几个孩子长大后学什么?做什么?走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选定的。他只是常对我们说做什么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做个正直的、积极向上的、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人。他的教诲伴随我成长,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经常在周末给我们开家庭会,每个人都要汇报一周的学习、生活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他带我们分析总结每个人的优缺点,也常常在家庭会上给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郝蒙蒙:外公是绍兴嵊县人,嵊县就是越剧的发源地。他说的也真正是吴侬软语。他叫小孩子都叫妹妹,不论男女。我叫外公为“阿公”。他很宠爱小孩子,虽然妈妈说他曾经是个严厉的父亲。
小时候,我常常冲进他的房间,把他的茶水喝个精光。阿公总是笑笑再添上水,然后跟我说:“妹妹,慢慢交喝。”然后,他拿出饼干给我。他房间的柜子里有一个匣子,里面放着万年青饼干。那味道,成为我甜蜜童年的一部份。
阿公往往跟我讲要做个好孩子,因为今天这一切来的不容易。他跟我说当年打仗的危险艰幸,可从来不说自已有多了不起。他只跟我说:群众有多朴实,多少人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让人心痛可惜。说到某一场战斗牺牲的战友……透过眼镜片,我看到阿公落泪了。
他真是一个心底柔软、个性刚强的人。
……
关于陈伯伯的故事与回忆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由于文章篇幅关系,这儿就不再展开了。
在此世界上,有着钢铁意志的肉体易逝,有着理想的灵魂永远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