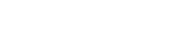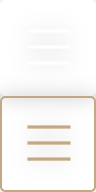宁波红色记忆
刊于《宁波市水文化》杂志
2020第04期(总第三十一期)
如水流年 缅怀“运河之子”黄源:“此生就为了说真话”(下)
车弓
四、民族危亡时刻,用笔杆子当“枪杆子”用的书生
在黄源多姿多彩的一生中,十三年的战争生涯占了很大的份量。他说:“战争浓缩了我的人生,使我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使尚还年轻的黄源热血沸腾,使他感觉到没有什么比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更为重要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去了鲁迅家,先生走了,他的夫人景宋(许广平)先生还在。他说:“我们的人们终于开始‘还击\\\\\’了,可惜站在民族解放战争前哨而苦战一生的鲁迅先生听不到了。但没关系,由我们学生在。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生的遗志,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坚定不多地走下去。”
黄源回忆说:“这时由于战争,邮路中断。上海的许多全国性大刊一律被停止发行。我把妻子(许曼华)和孩子迁回海盐老家,自己和茅盾、巴金、黎烈文四人,整顿原有的《文学》、《文丛》、《中流》和《译文》,先后以《烽火》和《呐喊》为刊名出版发行。”
同时,冯雪峰来“文化生活”找到他,要他为《鲁迅纪念文集》整理、编辑和校对。
这中间,黄源为老父辞世,回了一趟海盐老家。然后,他就义不容辞地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了新四军中光荣的一员。
他们是在浙江金华和中共东南局联系上的,由一辆大汽车把他们送到了皖南的新四军的军部。时间:1938年底。
黄源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1938年底,我们到皖南新四军的军部,第一天晚上,是个下雨天,东南局的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是政委)项英同志就在云岭接见我们,谈什么记不起了,但印象很深。当时我们是在军部参观,参观完,项英在元旦作政治报告,听光报告后,我就跟他到前线去了。”
“在军部、东南局,有邓子恢、袁国平,宣传部有朱镜我、李一氓……他俩我都熟悉,是前创造社的;项英、袁国平、邓子恢等军事首长,我却是第一次闻名。文化人中有夏征农、薛暮桥、聂绀弩、彭柏山、丘东平;这些人也都是熟悉的。但他们都分散在各支队里…”
“在新四军中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军政首长都是穿一套灰色的半新不旧、洗得很干净的军装,有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那时是新同志穿新衣服,老同志穿旧衣服),很朴素。另一个感觉是,我们在上海,在战争时期,生活是非常紧张的,相互关系却是复杂的。而我一到皖南,到共产党的军队里,真正感到这是一个大家庭。当时招待我住的房子,是一个三开间的民房,破烂不堪,可这是政治部的招待所。中间一间是空着的,点的是煤油灯,我住在里边,二纵队的政治部主任王必成也住在里面,非常艰苦,这已是相当于师政治部主任的待遇了。”
他写道:“在一支队待了好几天。我看陈毅和项英谈天,谈工作。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懂得他们在谈什么?其实他俩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他们两人一边谈天,一边吃桔子,买了两毛钱桔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举动了。”
在新四军留下来后,黄源的职位是《抗战》杂志的编委。《抗战》是新四军军部的刊物。项英1939年元旦的长篇报告就发在这里。一年后他由冯定和彭柏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他入党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做秘密党员,另一种意见是做一般党员。军部领导因考虑我已到了新四军,不可能再秘密,于是我就做了一般党员。
入党后,黄源担任印刷所的负责人。他说:“从1939年底,到1941年初,我都在印刷所工作。我工作得很开心,通读了六册《斯大林选集》,并在所里发动工人竞赛运动,我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黄源回忆说:“皖南事变发生在部队‘北移\\\\\’途中……”
“我们是晚上出发的,从云岭到章家渡,只有二三十里路,可是走到时已快天亮……那天路上我碰上画家赖少其,他在三支队。从三支队的地区,繁昌方向来,芜湖的外围是我们的部队。章家渡的青弋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是用马口铁箱和汽油桶连起来的。渡江后在茂林停下来。停了一天,再出发。都是黑夜走,打着灯笼秘密行动,白天怕飞机,本来是要往北走,但我们却往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
黄源说了那次“突围”中,他死里逃生的过程。他说:“叶挺军长被捕后,向组织上交待了一个清单,把我列入‘阵亡\\\\\’名单,大家都认为我死了。但我没死,虽九死而有一生,我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战斗是残酷的……”黄源回忆说: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这山口子是过去项英打游击时三四十个人通过的地方,叫丕岭。可现在有近万人的大部队要从这儿冲出去。这显然不大可能,部队刚到山脚下,就遭到敌人机枪的扫射,队伍就退下来。
总之,是冲散了。我们印刷所这次随政治部行动。天亮队伍集合时,我还忻到叶军长动员把教导队拉上去,我也跟着政治部的同志上山;可敌人占领了制高点……一阵疯狂的射击,又把队伍打散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山上很混乱,我插在一个不认识的团队里(后来知道是新三团直属队),跟着往下冲……
我们终于冲出来了,可是军部和大部队没出来,又往里缩了。这时冲出来的直属队走得很远了,只留下没武器的号兵和医务兵。我“突围”时军部给我配了警卫员,还有两支驳壳枪。我们用两支驳壳枪抓住了一个俘虏,是国民党四川部队的。这样我们就押着他一起走。因为是晚上,国民党部队远远地听到响声就问“口令”,我们就叫他回答。因为是四川口音,一路上没受到阻拦。
天亮时我们到了章家渡,和我一起突围出来的饲养员是本地人,带我们过江。敌人一阵机枪扫来,保护我的警卫员也被撂倒了,俘虏也不见了,我身边只有一个饲养员和小司号员。江边小店不敢留我们,于是我们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由饲养员带着我俩躲进老百姓的家里。
“因为附近村庄都住满国民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们在逃亡时和小号兵也走散了,最后只剩下我与饲养员两人,跑到宣城他家里躲了起来”。
黄源到了上海,先找老友陆圣泉。在文化生活社安顿下来后,第二天就去找了许广平,请她帮助我找党的关系。也仅隔了一天,就有人来找他,是在皖南事变前不久离开印刷所的陈昌吉,现在他在上海做新四军的联络员。他向陈昌吉汇报了突围到上海的经过。陈昌吉说:“事变后,不知你的下落,都以为你牺牲了。我现在马上把你的消息带到苏北去。”他问他以后怎么办?黄源说:“我想在上海呆几天,联系现在福建办杂志的妻子许曼华一起去苏北。”
他说:许曼华最后没跟他去苏北;从福建带来一封分手信,说要与他“永别”了。这样,黄源就自已去了苏北。
几十年后(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入日籍的许曼华来杭州拜访黄源与巴一熔夫妇,说起往事,不胜吁嘘。
黄源在华中局参加第一个会议,是宣传部的内部会议,政委刘少奇参加这个会。他在会上强调:在宣传工作中,办好印刷事业是战略性的任务。在抗日大局上,笔杆子可与枪杆子并用;或在特殊环境下起到枪杆子不能起到的作用。这对黄源来说,是一种鼓励,在民族危亡时刻,居然司以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使用。这可是中共高层领导说的话呀!
令黄源印象深刻的是:左翼文艺战士丘东平,在率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师生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黄源初到根据地后,在华中党委宣传部彭康的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文委”。一段时期后,组织上要他接替丘东平任鲁艺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分院的院长由政委刘少奇兼任,教导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黄源在回忆录中说到:“丘东平是左翼作家,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个老红军,参加过红军长征后坚持南方的战争,新四军老干部,参加过上海吴淞口抗击日寇的战斗。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主要因素还是考虑到他的创作,因为他想把红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经历,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我接替丘东平教导主任职务时,正值敌人“大扫荡”前夕,我向陈毅同志请示:‘工作上要注意什么?\\\\\’他说:‘你要有魄力地干。第一个任务是带全体师生下乡,少奇同志指定盐城五区为你们下乡地点,这是华中局农运工作的试点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全区农会,限期一个月完成。\\\\\’为了使我们应付恶劣的环境,更好地完成任务,陈毅派了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团级军事干部,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1941年7月,敌人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伪动用了1700人、兵分四路合击盐城。黄源接到华中局的通知,把鲁艺分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院部和文学系和绘画系组成,由他带队随军部行动。第二大队以音乐系、戏剧系为主,由孟波、许晴和丘东平带队……
黄源说:“这样,我们第一大队在湖垛待命,第二大队奉命奔赴五区。下午经过湖垛时,我还去路口为他们送行……次日下牛,二大队一小部分师生突围出来向我报告,他们行写到北秦庄时遭到敌伪伏击,伤亡惨重。丘东平、许晴两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丘东平已冲过桥头,在河边指挥队伍向被枪弹封锁的桥头突围时,被敌人子弹击中……”
“我立即把情况向军部报告。陈毅军长对我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文艺战士很不放心,派了一位团级军事干部与我们一起行动,随后,又把鲁艺一大队编入三师的黄克诚部,随大部队一起行动。”
这次“反扫荡”结束后,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黄源参加了华中局整风小组。他说:“小组的组长是曾山(也是调查研究室的主任)……通过学习,我提高了认识,对鲁迅先生也有了新的认识。三十年代我看他的原稿,发表他的作品,只是觉得有道理,说得透彻。但是道理的原则是什么?并不清楚。后来,曾山同志对我宣布:‘对党的政策是理解的,但还没有通过实践,要在实践中来考验。\\\\\’”
这时,黄源除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外,还收获了爱情。他在盐城意外地碰到了巴一熔。她1940年就到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办《战斗报》,他俩在皖南军部时就熟悉,巴一熔还当过印刷厂的指导员。
1942年12月23日,黄源在下面一个县开展工作,突然接到华中局组织部曾山急函,调他和贺绿汀、阿英立即回军部。因事关紧急,黄源没等贺绿汀和阿深,独自带了一名警卫员骑马赶回军部。路过三师驻地,师长黄克诚告诉他:“你赶快去追,军部25号就要走了。”这时黄源才知道“紧急情况”是这个。
黄源去浙东开展根据地的活动,是彭康向他传达的。
黄源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做了许多工作,多年后,他总结说:“我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在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员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当时在浙东的国民党杂牌军有88团田岫山(“田胡子”)、89团张俊升(张胡子)的部队,经过我的努力,“田胡子”虽然没有“改邪归正”,后来还是投靠了日本人;但为我们在四明山区‘落脚\\\\\’,争取了时间。而张俊升的89团,后来成了我们自己的人。”
黄源说他在浙东抗日根据地,重点做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包新旺在《黄源传》一书中写道:“浙东地区是‘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不拘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富有创新精神。浙东一带经济文化发达,统一战线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源到浙东第一年,住在四明山下的杜徐村,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下着大雨,群众都走散了;而‘的笃班\\\\\’的锣鼓一敲,群众又纷纷地赶回来。寅源没有想到,民间戏班子会如此受群众欢迎。当时,根据地的所有武装力量加起来也就七八千人,可是民间艺人竟然有一万多人。”
这使作为文化人的黄源想了很多,如何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为抗战服务?这使他想起“高升舞台”,这是当时留在根据地唯一的一个“草台班子”,黄源就让韩秉三(高岗),刚从华中鲁艺音乐系毕业的王斯苇住进剧团去,还让和老艺人接触较多的伊兵筹建越剧团。在杜徐村组建了鲁迅学院和成立了“社教工作队”,举办教师训练班,改造民间艺术,直接为“抗战”服务。这些群众文化活动性质的文教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活动。
包新旺在《黄源传》中,还提到一件事。一天,黄源在三七市听到一个破庙里传出拉胡琴的声音。走近一看,原来是四个人在说大书。他就动员他们参加社教工作队,说自己创作的新书。在他的指导下,说书艺人以鄞县女区委书记李敏的事迹为材料,创作了剧本,将烈士生前的现实生活、牺牲精神都演绎了出来,非常感人。
关于浙东鲁迅学院,黄源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浙东行政公署建立前,我们的教育工作开展不力。一是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例如三北地区的校长,都是国民党委派的,但委派后却很少去管理。二是根据地缺乏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骨干。他说:“鲁迅学院就是抓这两个中心问题,指导思想很明确。”
关于鲁迅学院的作用,黄源举例说:“我们的浙东鲁迅学院,有的学院原来是在国民党地区的浙大读书的,暑假回来看到有这个学院,假期满时就不愿回去了;进了我们的学院……”
“浙东鲁迅学院出过不少人。有的后来当了副军长,乔石夫人翁郁文,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家的,她也是在鲁迅学院入党的……大部分学员参加了浙东部队,后来就成了华东野战军的20军……”
1945年初浙东行政委员会建立,成立了文教处。已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源,担任行署文教处长。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黄源跟随陈毅等首长征战沙场,参加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鲁西南突围,最后,一直打到河南许昌。当然,文人从军,他主要还是负责军中文化工作一块,为保护这位鲁迅的学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首长都为他配了两位警卫员。
包新旺的《黄源传》中写道:华中部队“七战七捷”后,黄源在机关待不住了。他找到华中局第一书记兼政委邓子恢,要求上前线。邓子恢说:“你去做什么呀?部队打仗,你发挥不了作用,人家还要照顾你。”恰巧,这时张鼎丞在场,他说:“到部队去也好,我给你写介绍信。”说着,他拿笔给陶勇写了一张介绍信。这样,黄源就到了陶勇的部队。”
1947年元旦过后,陶勇的部队打下国民党的快速纵队。次日,天下大雪,黄源跟陶勇一起到战场上去查看,但见满地放着千疮百孔的汽车、破破烂烂的坦克。他们正检查战场,陈毅赶过来了,看到陶勇就喊:“快、快,马上进攻枣庄!”
在枣庄,陶勇一共打了十一天。由于是攻坚战,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见成效、大概打到八九天,粟裕来了,陶勇问:“打不下,怎么办?”粟裕说他回去问陈老总。陈毅说继续打,从叶飞的一纵队调来张文碧的一个师。最后总攻时,又调山东八师会搞爆破的部队一起打。总攻那天,粟裕来到陶勇的指挥部指挥三个部队,那天黄源待在他的身边,粟裕在电话里讲一句,他记录一句,从总攻开始到全歼敌人,是一个完整的战斗记录。
枣庄战役结束后,我军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了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和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六万人的“莱芜战役”重大胜利。
接着,5日11日晚上,军部决定打七十四师张灵甫,叶飞派谭启龙、何克希各带一个师,插入对方两个师之间,叶飞也带了两个师形成包围圈,切断了七十四师同外面的联系,无奈之下,张灵甫只好上了孟良崮。
到了总攻时间,叶飞下到师指挥部去了。军部只剩黄源和完成包围圈后回来的何克希。黄源既要接听陈毅的电话,又要保持与前线的联系,传达陈毅的命令。最后一夜,形势非常紧张,根据陈毅的指示,叶飞命令从狙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叶飞果断下令:“你给我冲,整个建制打掉也要冲,不上去,杀你头!”各路纵队就漫山遍野地冲了上去。下午六时,张灵甫的尸体便被放在一块木板上从山上抬了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黄源跟随叶飞、陶勇等赫赫有名的战将,参加了枣庄、莱芜、孟良崮、鲁西南突围等战斗。特别是叶飞,他与他相处时间很长,私人友谊也很深。
五、“由来物性难理说,有不为焉有为之。”
1983年底,中共浙江省委因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三月底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精神,通过了彻底为黄源平反的决议,全文如下:
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
开除黄源同志党籍决议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黄源党籍的决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根据党的政策,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对黄源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复查。黄源同志不存在当时所谓浙江文艺界反党集团为首分子的问题,不存在敌视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的问题,不存在煽动文艺界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因此,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关于开除黄源党籍的决议,是错误的。现在,对黄源同志的错误处理,已经改正,彻底平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已经得到恢复。
代表大会致认为:原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省委决定予以改正,是完全正确的。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黄源党籍的决议》。
黄源读完刊登在《浙江日报》上的省委决议,黄源脸无表情:“平反复平反,平反何其多”,这一回,现今终于到来了,他怔了一阵子,突然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号啕大哭起来……
其实关于右派的“纠正”,已经有两次。一次在1960年,另一次在两年前,说是摘掉他头上的帽子了,但恢复党籍。盼望已久党员生活,却是刚刚开始。接着,他被安排为省顾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全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丁玲、艾青、楼适夷、巴金、贺敬之、叶飞、谭启龙、刘白羽、夏征农、萧军、周而复等人多次来杭州,踏着葛岭的石板路,摸着西湖山色,前来看望他们的老朋友。
一天,省委书记江华专门邀请黄源去西湖国宾作下棋。两人棋逢对手,足足下了三个小时,最后,好一盘“和棋”。
临走时,他送黄源一张照片。黄源收下了,他知道,这是他所经历的时代中种表示“和解”的方式。
“老子打儿子”,这是那个年代普遍的“说法”。可是,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二十三年,一寸光阴一寸金,他都在经受批斗、劳动、坐冷板凳,在屈辱中度过。他的家人也无不受影响。巴一熔生的大儿子黄放放高考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却进不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在浙大毕业后,还到四川农村待了十年,入党根本就不可能。另一个儿子黄明明参军政审不合格。连他打成右派时才七岁的儿子黄平也受到歧视,入学受阻,后来下放到农村,迟迟不能回城。
对此,“平反”后的黄源感慨万千。他在“自传”中写道:
“建设新中国没有经验,交点“学费”可以理解。但是,学费缴得太多、太久,反复地缴,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有些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各种问题要缴的学费也不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经验,可以原谅,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可以说古今中外的领导人都曾有过经验教训,实在是可以吸取的。”
黄源在鲁迅、茅盾领导下工作10年,在陈毅领导下工作17年.离开他们调到浙江工作才两年,就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了;耽误了23年宝贵的时光。
可这一切,都是为了“讲真话”。
平反后,黄源赴北京拜访茅盾,当年勃勃青春汉,如今一把老骨头。两人相互对视、握手、拥抱,岁月无情、不胜吁嘘。
茅盾提笔给他写了个条幅:
蝉蜩餐露非高洁,蜣螂转凡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有不为写有为之。
黄源曾说:“这首诗,‘诗眼\\\\\’在第三句上,讲自古以来世上有不少事物,你就是满身是嘴,都说不清楚的。”
黄源一直记得他与巴金的交谈,表示不管以前经历了什么?希望把晚年的精力多用在学习、研究鲁迅的工作上。多写回忆,多与笔记……因为,知情者实在是不多了,而在鲁迅最后两年生活中,自己是接近他最多的一个人。
“及时已见太平来。”黄源从部队下来地方,第一站是“十里洋场”的上海。
那时,他踌躇满志,试图大展宏图。因为,跟随陈毅市长接收上海的“队伍”中,像他这般跟随鲁迅、茅盾10年,又在战争年代和革命熔炉中锤炼过11年的干部不多。
黄源是随着“三野”解放大军进城的。他惦记着巴金,进城后稍作安顿便去找他。相隔十多年,这对老友终于又见面了,黄源告诉巴金:及时已见太平来。他要代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去接管上海的文化工作。
不久,黄源被安排在上海军管会所属的文艺处,夏衍任处长,他任副处长兼党组书记。接管工作由上海市委领导,夏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源是部文艺科长。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黄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而那年,黄源也才四十五岁。
如果按正常了发展,作为鲁迅的“入室弟子”,又经历过战火考验、有着十几年党龄的文化人。他的前景会随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业发展,变得一帆风顺。但是,黄源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始终坚持着鲁迅先生贯穿一辈子的思想见解,即:“活着就为了讲真话……实在没必要放弃自身尊严,去迎合某一群体或个人。”
是的,在鲁迅身边呆了那许多年,又经历了战争场面的考验。黄源觉得自已没必要去迎合别人。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的中国文化界的“界别”,出于周扬、夏衍和冯雪峰之间的“恩怨”。1936年,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恢复党组织的关系;而他,没有找所得的“自己人”的周扬和夏衍,却找了鲁迅。据了解,那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有历史学家认为:“周扬、夏衍与冯雪峰、鲁迅及鲁迅身边的人隔阂由此产生,并伴随他们漫长的一生。
自然,这是后话。当时的黄源是不知道的,他只是像一头充满激情的雄狮,全身心地投入城市文化复苏中。而没提防从身后射来暗箭。
1981年6月,夏衍到杭州休养,黄源陪同他游西湖。夏衍刚想说些什么?被黄源摆手阻止了,黄源不提防提到解放初期,两人在上海的工作,夏衍也不让说下去。黄源与夏衍,如果从现当代文学史角度看,是一个较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从五十年代夏衍力促《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十五贯》的社论,到八十年代两人相互通信、相互勉励,结伴畅游西瑚,以及此后解密的诸多文学史实,使得这一课题豁然开朗,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武训传》事件,发生在黄源任副部长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上海,尽管他没有参加影片的前期策划和制作,但与他却不无关系。
黄源回忆:
“我能请了赵丹和编剧,同饶漱石一起看。饶漱石看过以后,他也没说什么。我看了后,觉得当时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搞办学,戏里有这两方面的场面,觉得有一点改良主义,不是一个单纯办学的片子。我们是从武装斗争出来的,深知办学本身当然是好的,但是,要用办学来救国,来解放中国,像武训那样是不行的,而其教育内容又是宣传封建主义的,这是当时闪过的念头。我后来看到毛主席写的文章,提到批判什么,歌颂什么的高度,我正当时也没有想到。”
夏衍回忆:
“……我准时到会,令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感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竟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声说‘好、好\\\\\’,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的这一表态,实际上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 (夏衍:《懒寻旧梦录》)
读者可从这回忆的度不尽相同、特别是饶漱石看完影片的态度中看出端倪来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对“电影《武训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热潮,最后由周扬要夏衍代表上海文艺界作检讨,毛主席看了后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与上海文艺界;“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解放日报》办了一个简报,其中有一期揭发华东文化部有官僚主义作风。当时华东文委的主任是舒同,秘书长是徐平羽,问黄源:“你行吗?”黄源说:“我怕什么?不贪污、不腐化,没搞个人什么东西。”
然而,黄源还是作了认真的检查。那时候,干部都还自律,黄源是九级干部。按正常,他可以定七级,但他自己圈了个九级。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部长是陈望道,但他参加复旦大学教授评级,黄源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实际主持文教部的工作。
他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他重建和重组了剧团,进行戏剧和戏曲的改革;还开展文物工作和筹建了上海博物馆。纵观他在上海的五年工作,陆定一和陈毅、还有华东宣传部的评价:主流是好的,正确的,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起的;缺点是经验不够、魄力不大,观察党的方针不够有力。
1955年5月,疲惫的黄源踏上故乡的土地。这时他的心情是欣喜的:游子还乡,可以在这块他所熟悉的土地上施展手脚。同时又是复杂的,那时他已隐约地感觉到,讲真话与现实的矛盾。但是,他还是必须说真话,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
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黄源负责浙江的文艺工作。
黄源在浙江,先在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后任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重点干了三件大事。一是经过调研,从当时的浙江实际出发,重点抢救和发展民间艺术(重点为戏曲和工艺美术)。这段时间里,全省84个县、市分别举办汇演和参赛节目三千余个,发掘、抢救民间艺术节目一万多个。二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戏改政策”。根据1956年6月统计,全省共有剧团121个,几乎各县都有,有些县甚至有多个。各地方剧种经常演的传统剧目有1452个,剧场有114个。三是抓了浙江省的文学创作队伍。作为三十年代上海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黄源对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情有独钟。在他的主持下,办起了《东海》、《群众演唱》、《俱乐部》三种杂志,创办浙江戏曲学校、浙江民间歌舞团,改编昆剧《十五贯》和保留提升了省苏昆剧团先、建立省电影制片学校、恢复西冷印社等。他在1956年10月创办的文学月刊《东海》杂志发刊词上号召作家要讲真话,说:“善于歌颂,勇于批评,这是我们创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标之一。‘死样活气\\\\\’的八股文章,不被读者所欢迎,不容说的了。”
与晚年黄源有过多次接触的原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行回忆说:“黄源同志善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特别是对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非常爱护和尊重,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帮助、引导,使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样一种蓬勃向上的艺术环境当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家。他交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跟他们像家人一样,非常亲切,非常亲密。使得这些艺术家时时都能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
在盘点五十年代文化浙江的家底时,昆剧《十五贯》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黄源主政浙江文化工作后,发现昆曲这一古老的剧种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艺术传统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便开始关注了。1955年底,田汉到杭州,黄源陪同他看了苏昆剧团的演出,演员精湛的演技,给田汉留下深刻的影响,他向省长沙文汉建议,让该剧团进京演出。在沙文汉的支持下,黄源与厅文艺处长郑伯永等人,经过20几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把苏昆剧团的旧戏《十五贯》,改编成一台主题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新剧目。
从整体上看,改编后的《十五贯》不仅透露出浓厚的民间趣味,民间感情和民间意识,同时也寄托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美好想象。1956年1月,该剧在杭州公演三十余场,接着,春节期间在上海演出,结果场场爆满,观众反应十分热烈。1956年4月5日,刚转为国营机制的省苏昆剧团携该剧赴京演出,4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欢看了《十五贯》。第二天,毛主席就派人到昆剧团传达指示:“一、祝贺《十五贯》改编和演出成功。二、要推广,凡适合演出的,都要根据各剧的特点演出。三、对剧团要奖励。”
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回来后,也马上看了《十五贯》,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阅过许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当年黄老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证据”。按常规和现存资料的说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当年“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省长沙文汉,作为文化局局长的黄源和省文联主席宋云彬是“陪绑”。
宋云彬是有材料的:
而黄源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他能够“谨慎”一些,违心地说一些“场面上”的话,与界定的“目标”保持点距离,这右派是划不到他头上的,虽然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不乏向他打过招呼。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传达全国省委书记会议精神时说:“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尤其是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过不去的……在反右问题上,尤其对宋云彬的问题上,有些人是温情主义,实际上是右倾。”
并特别提醒:“整风中要有什么就揭什么,不管他头发多白、资格多老。”事后大家明白,“他”,就是日后成为 大右派的沙文汉。
因风寒引发心肺性疾病,沙文汉于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死时才56岁。临终前一天,统战部长向中央请示后摘掉右派帽子,几近昏迷的沙文汉努力说了声“谢谢”。这成为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尽管如此,黄源仍没有说违心的话。所以把黄源只能是被右派了证据如下:
1、文艺宣传资料不是创作。
2、我一听到四明南词就沉醉了。
3、光想着当官,是没有出息的,也可以当“专家”。
4、把艺术还给艺人。
5、现在我们靠陈静(编剧)吃饭,没有陈静,越剧团下半年没饭吃。
7、浙江文化发达,遗产丰富、我死也得死在浙江。
……
就这些“证据”,把一个党的九级干部“拿”下了。
我退休后两年,也就是2014年吧?我的师友、原省文化厅厅级巡视员、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廷竹携夫人前来宁波探望我,说起黄老复出后对浙江文艺界的贡献。他说:“八十年代初,我有个发表在《江南》的中篇小说《希望》被批,是黄老、高光等老同志站出来说话,保护了我……后来,又是黄老介绍我去了他曾经战斗过的部队,使我有幸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莅临‘老山\\\\\’前线,写出了许多有生活经历的军事文学作品……”他说:“黄老是个好人,晚年扶持了许多年轻作家和艺术人才。”
与廷竹老师一样,浙江和全国,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时刻,缅怀此生都讲真话的黄源先生。
真话不朽,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