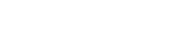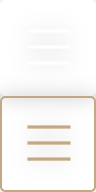前言
去年,母亲在我们家住了四个月。除了看点书,也闲着无事。我们就劝她动动笔,写写回忆录。开始,她不太愿意,认为白己不值得留同忆录。我们说了许多好处,主要有二:一、为过去留点痕迹,留个纪念。以后,我们想起她可以拿出米看看。二、动动笔,可以练脑,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她不怕死,但最怕得老年痴呆症。那样,生活不能自理,怕麻烦连累我们儿女。于是,说动了她,她开始写了。哪知她一写起米倒很认真,而且兴致越来越高。有时中午都不休息。
三个月时间,写了近四万字。
应该说,我们是了解母亲的,但了解得不深。这回忆录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了她。首先,她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员。确实,她为自己、为家庭想得很少很少;一切,以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为重。以至于我们儿女辈在一些地方对她都很不满。再则,她是一位非常坚强的人。她的一辈子,受压迫、受压制的时间多,灾难多。年幼丧父,家境贫困。更要命的是因家无兄弟“继香火”,母女俩在封建社会受尽白眼革命年代两次被捕。解放后,一直受党内极左路线的迫害、压制,“文革”中更不待说。中年丧夫,老年失女。这一辈子所受的艰难困苦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但她硬是挺过来了,而且极少对人言谈。就是回忆录中,也谈及不多。母亲的一生不容易。
母亲己八十高龄,又多病,真是风烛残年了。我们无法使她诸病消弭,但我们希望能慰安她晚年于万一。我们编印她老人家的回忆录,以为她八十的寿礼。祝她老人家能多活几年。
楼近水/王小平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
我的一生
文/贺思真
一九一九年十月,我出生在镇海江南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封建意识浓重。父亲以小贩为生。由于身体多病,不能全天经营。幸而母亲手巧,靠给人家做缝纫针线活等收入来补充家庭生活费用,但也难过温饱之日。
在旧社会,女性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没有男孩子的家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家。因我家贫困,又因我是一个独生女儿,父亲死后,母亲终日苦恼,总认为家中没有儿子,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对母亲的苦恼,随时记在心里。有一天,我安慰母亲说:“等我长大,我一定赚钱给你用。”母亲说:“女人能赚钱,什么难处都可以解决了!”
我十一岁那年,由于大舅父家的子女都在七、八岁就上学读书了,外婆就对我母亲说:“我只有这一个外孙女,到十一岁还没上学,你把她叫到我家来,我出钱给她读书,吃饭跟我一起到二个舅父家吃。”我听了多么高兴,每天想读书的愿望实现了。与表兄表姐一起学习、读书,这是我从小以来最快乐的时间。
二年后,母亲为了没付饭费给舅父,觉得过意不去,同时,我不在她身边也缺少一个缝纫针线活的帮手,就把我叫回家。那时我是多么的难过,但想到母亲的处境,也就同意了。
同到家后,听说离我家一里多路的地方也要办学校了,我就要求母亲给我继续读书。母亲答应我的要求。就在我十四岁上半年又到初级凤洋小学去读书了。
这个学校是二个班级,三个老师。校长姓林,四十岁左右,白脸、中等身材,戴眼镜。二个老师:一个姓虞,身材魁梧,脸黑,很有精神,是三、四年级的老师;一个姓郑的老师,教一、二年级。我到学校见到学校很小,没有操场,觉得与我外婆家学校相比,实在差得太多了,但因为有书读,我也高兴。进校读二B后,觉得老师、校长对学生和蔼可亲。课余时常问长问短,问家庭情况,问学生兴趣等。在公民课时,讲苏联革命故事:在每周周会时,还讲国家大事和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等事。特别是林校长气愤激昂的讲话,更激起我们爱国和对日本鬼子仇恨的情绪。虞老师教我们唱打倒列强,救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和“九·一八”等抗日歌曲。到双十国庆节,我们三、四年级同学还到五里外的大契头镇上新庙集合游行,高喊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比我们大的学生还到新街口商店搜查日本货,把抄出来的日本货当场烧毁,搞得抗日爱国热情非常高涨。
三年级读了半年,由于我读书用功,成绩优良,品德评为优秀。老师对我说:“你下学期读四年好不好?”我想少读一年,初小毕业后,我可以到外婆家去读高年级,我就同意。
初小毕业后,人家议论我母亲:“饭也吃不饱,还给女儿读书,将来也靠不了女儿的。”母亲听了此话,就坚决不让我再读书,说:“没有儿子争不了气,女儿不读书是可以争这口气的。”我就失去了再读书的机会。可是我并不放弃学习。把旧课本反复学习,把三年级下册未读过的书向同学借来再自学,还规定每天起早练习写毛笔大字。
后来知道,林:虞二位老师是地下中共党员,虞老师被国民党逮捕,林校长被国民党通缉。我想,这二位老师是共党员,那共产党员不是很好吗?我就对共产党员留下了很的印象。
我小舅父五十岁生了一个儿子,我母亲高兴地说:“我哥有了后代了。”因为小舅父是在客轮上当厨师,经济条较好。舅母产后身体也不很好,就把我叫去给她家帮忙抱孩子。因为母亲高兴,我也愿意,就到舅母家共同养小弟。在原来学校读书的同学也可高小毕业了,学校里的校长,教师都调换很多。听她们说,现在学校的校长是很开明的, 比过去胡老头校长思想封建,重男轻女,专门拍地方士绅马屁。现在校董也调了年轻的。学校里还买了许多新书。我果要看,她们去借来给我。我高兴极了。可是学校已将放假,她们忙于考试,阅览室也要整理,没有借来。但在我思想上已有了个看书的愿望。
暑假里有一个姓李的女教师,来叫我做一件黑色丝绸旗袍。这位教师很好,我对她谈起读书、学习,我羡慕她有独立工作等。她也告诉我,妇女要自立,必须要自己努力奋斗等等。
二七年月七号,日寇侵占卢沟桥后,全国掀起抗日风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的镇海江南也与全国一样,抗日救亡团体似雨后春笋般的风起云涌,抗日歌曲到处可听到,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日益高涨。我抱着小弟弟到处看抗日救亡团体的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剧,“流亡三部曲”的抗日歌曲,更唱得群众泪流满面,我也坐不住了,参加了抗日的救亡活动。
一九三八年夏天,经过李老师介绍,我要去参加镇海县举办的妇女救护训练班。我征求舅父舅母的同意并说服了母亲,就跨出了家门奔赴镇海县城,参加妇女救护训练班学习,准备上前线为抗日战士服务。但训练班毕业后,仍没有上前线的机会,又回到舅父家。
母亲是很高兴的,要我安份守家,说:“你小舅父早说过不会多你一口饭的”。可我的心比过去更安不下来了。一面仍给亲朋好友缝衣、绣花,一面又去寻找指导我前进方向的李默君老师。她原在我母校延陵学校教书,后来到汇南新民小学去了。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她。我对她诉说后,她指导我说:“你可以到延陵新办的夜校去读书,那里的老师、校长都很好,我有机会对他们说,他们会教育指导你的。”
回来时,她借给我一本《女战士丁玲》。我回来后,捧着这本书反复阅读,思考,对这位女战士敬佩、羡慕至极。我到夜校去报名,要求读书。夜校老师确实很好,我报名时写了姓名,他就说:“你是贺佩芳吗?李老师告诉过我们,你和我们学校的贺校长是同姓的。”态度很和气,不收学费。但女的青年读夜校的很少。一学期后,夜校老师动员我到延陵学校读全日班,学费免收。我回来征求舅母同意,并保证白天家务晚上完成。我高兴地又回到母校读书,读高年级毕业班,与李雅琴(李敏烈士)同校同班同桌,并为好友。
一九四零年春节过后,学校开学的一天,校长张谦达,高年级班主任邢韫辉和历史、地理老师王忠孝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校长说:“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们又增添了新的同学,新、老同学互相学习,团结一致,把我们学校办成既是学业成绩优良,又是乡村抗日宣传教育的典范学校。”随后学校又成立学生会,选我为组织委员,李雅琴为宣传委员。
学生会主席选出后,因患病到外地求医,学生会的工作实际上落到我和李雅琴及生活委员的身上。我们在老师的指点下制订了一个计划。在校内,每周末全校时事演讲会,高年级有学习讨论会。在校外每周二次出时事墙报,每周一次到街头、村上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教育,还到村口动员高年级同学参加陶行知先生创导的小先生制活动(如帮助妇女识字写字利写家信字条等)。还建立医务室和校外医疗服务队等等。把抗日宣传教育从学校到校外搞得轰轰烈烈!就在同年四月,学校党支部找我谈话说:“你进学校后,团结同学,学习努力,把学校的学生会工作搞得很好,做校外的抗日工作也起了积极带头作用。我们支队原就知道你要求进步,又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救护训练班,要求你到学校来起学生的骨干作用,经过几个月的锻炼,你确实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学校支部研究决定,吸收你为中共党员,没有候补期,因为你是贫苦家庭出身。支部并分配你任务,把李雅琴做为培养教育对象,对她进行培养。”
在秘密地区入党是没有自己申请书的,只有共产党来找你,你是找不到共产党的,并且大都是个别吸收党员,入党介绍人也只是个别向你说明,因为党员面目暴露过多,容易出问题。那时,我对党的认识是很单纯、很肤浅的。我只知道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是积极抗日、坚决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共产党员好、共产党一定是好的。经过抗日斗争的教育,我对国民党是非常痛恨的,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把东北三省让给日本帝
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侵占中国。“七·七”芦沟桥事件,“八·一三”进攻上海,广大国土沦陷,人民大众作亡国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此我要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由邢老师在一个小间叫我进行个别宣誓:一张大红的纸上,画了镰刀斧头作为党旗。刑老师与我共同举起右手说:“一切服从党组织,努力为党工作,必要时要为党牺牲个人生命。”从这天开始,在我的思想上就牢牢记住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一切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入党以后,我的奋斗目标更明确,精神更振奋了。后来知道张谦达校长是当时镇海江南的县委书记,刑韫辉是我校支部二日记,王忠孝(现为北京国防大学教授即王剑君)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党支部的。
学期结束,校长老师决定我与李雅琴都留校办暑期班。不料,七月五号的拂晓,日寇从我校附近一里左右的海岸上(俗称老鼠山)登陆,我与老师等都在学校准备办暑期班事,听到枪声,就即起床离开学校到对面山头隐蔽。看见日寇一路疯狂烧杀,路过我校,见无一人就用火药枪把我们前后二幢美丽的高楼点起烈火,烧成断墙残壁。我与老师们都抱着愤怒的心情,一定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寇,。大家互相约定联络地点,就各白回家或投靠亲友。
这是日寇第一次登陆镇海。半月后被我军击退。
同年八月,党组织来通知,要我到镇海柴桥镇一个学报到,到达目的地后,接待我的是我校王忠孝老师。大家相聚了,很高兴。他告诉我:我们参加的是“定海国民兵团随军服务队”,该队是我们地下党员负责人与定海县县长苏本善搞统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一九三九年定海沦陷后,苏本善流亡到镇海柴桥,他为树立自己的政治影响,我党为建有群众阵地,扩大我地下党的基础,就成立这个队。该队队
长为干烈君(即乇起),副队长杨监清(实际负责),二十几名队员,其中中共党员有三分之一,其他是要求进步青年和原在各地政工队退出来的从流动施教团来的,也有中小学教师。队伍里人才济济,会画、会写、会唱。先在柴桥镇集中一段时间,把柴桥镇抗日气氛搞得热火朝天。白天到群众家串门、贴标语、出墙报。晚上街头宣传,到庙院祠堂演出革命短剧。最重要的是与当地的地下组织配合,了解各阶层情况与地方士绅、镇氏妇女会等群众团体联系,把整个情况掌握在我党手中。
一个月后,因离柴桥二十里外的郭巨乡也有苏部驻地。经苏部要求,把我们分成二个组。我们与队本部一起为第一细。在柴桥,我们的工作分为二方面,男同志向部队士兵做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女同志做地方群众的教育工作。女同志虽也有五人,但党员只有我一个。为配合该镇原妇女会工作所以把我与陈弧同志留下在柴桥,叫我负责地方工作。该镇妇女会会长是一个小学教师,丈夫死了,就留下一个女孩,生活较为清苦,但为人直爽,在镇上也有一定的威信。我们通过她了解镇上各方面情况。我很同情她,与她也建立了较好的感情,她的女儿对我也很有感情。她长我九岁,我们为了更广泛团结联络各上层妇女,在柴桥镇办了一个“柴桥妇女合作商店”,因为当时宁波被日寇封港,上海等货物大都通过舟山、穿山等地,因此,柴桥成为“小宁波”。妇女合作商店成为联络感情,了解情况,进行抗日宣传的场所。地方士绅的太太和部队官员的太太都成为合作商店的股东,各方对合作商店帮助很多,生意很兴旺。等我们离开柴桥后,该商店经理由妇女会长王佩兰负责。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来还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在基层妇女中成立妇女识字班。帮助芦江庙一带“送娘子”等贫苦妇女提高阶级觉悟,热爱祖国,懂得当亡国奴的痛苦耻辱等生活,树立妇女自强不屈精神,努力学习、劳动自立的重要等,以文化教育来达到政治目的。
在柴桥半年多来,虽然也经过飞机轰炸,受国民党特务人员的监视等种种困难,但广大群众对随军服务队留下了较好的影响。
全国反共形势紧张(正是皖南事变)也反映到我们的随军服务队。一九四一年二月,定海国民兵团名为到武义整训,实为削弱地方势力,要我们随军服务队跟部队一起剑武义整训。经过党中共宁属特委决定:“留下个别党员,坚持在苏本善处,人多跟部队去武义整训,但要保持整体组织。”
四一年二月,从柴桥出发,每天跟部队行军,步行60公里以上,经过鄞县、奉化、新昌、嵊县、氏乐、义鸟、金华直到武义。到武义后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等教育活动。写标语、出墙报、演抗日剧等。因语言不懂,也碰上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反动当局要将随军服务队取消,把人员分散到各部队去,我们支部研究,随军服务队存在我们坚持下来,要取消分散到各部队去,我们坚决要回原来地方。经过多次说理斗 争和要求,结果每人发车船费和少数生活费,放我们回归。
在金华车站,刚逢日机轰炸,就在夜间乘车,沿途经过诸暨等地。见轰炸后的一片焦土气,到绍兴见到白色信号弹,
知道日寇进攻,立即乘脚划船连夜奔赴宁波郊外,可是宁波城区已被日寇占领,就随逃难群众从宁波南效又往奉化松岙,因为松岙有我们的地下党员,经过了解,我们原来的定海国民兵团已经在鄞县咸祥大嵩一带,准备向象山进发,我们就绕山越岭,没吃没喝直奔大嵩一带,找到原留下在苏部的支部委员王忠孝同志。虽说我们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与 饥饿、脚上血、泡、手臂刺破、衣衫破烂。但能见到他们,我们内心还是非常愉快。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欢迎我们胜利归来。但我们回来正是日寇第二次在宁波、镇海、奉化、绍兴等地全面沦陷。柴桥当然也陷于敌手,为此,由王忠孝请示,中共宁属特委指示“要王向苏本善表弟朱铁军建议,可以成立敌后青年突击队”。经过多次与朱铁军商讨后,就用各县的名称为“定、象、镇、鄞四县敌后青年突击队”范围规模大,我党就利用这个机会调集党的骨干,如奉化谢仁安,鄞县的孔令汾加王忠孝和方云庆等,为该队伍正副队长及党组织支部,组成人员有百余人,下分镇海分队、鄞县分队、 象山分队、定海分队。我为镇海分队队长,我们在大契镇上 设立办事机构。
我队共有十余人,吃住各人分散在群众家里,工作又集中又分散,出入又公开又隐蔽,主要以发动、教育群众提高觉悟,保家卫国,打击来犯敌人,搜集敌、伪、顽动态。特别是依靠基层群众,宣传我党宗旨,扩大和打下我党的基础,发展我党力量、扩大我党影响。
青年突击队从四一年四月成立到八月,四个多月中在镇海、鄞县队,各队作了大量工作,在教育群众、共同协助部队、打击日寇扫荡、抢粮等方面起到主要作用。大协助地方治安阻扰坏人坏事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在敌后尖锐复杂的环境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有些队员在襄暑不稳定政权的情况下,勾结坏人作坏事,引起队员部队之间矛盾激化,互相残杀,被坏人打死一个队员教师。更为深痛的是我们党的骨干副队长到宁波敌占区执行任务,被原在国民兵团中的投敌分子出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严刑逼茛,要他投敌,他坚贞不屈,后被日寇狼狗狂咬惨死(现为烈士)。也有委派到镇海县城里去作情报和策反伪政权工作的队员,怕过紧张和危险生活,后来脱离抗日队伍回家结婚等情况。
同年八月,根据全国形势需要,中共宁属特委决定:“有条件的地方要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江南县工委就以王贺乡长王博平(地下党员)的名义组织乡武装队伍,同时抽调在青年突击队中的党员和青年进步积极份子20余名组成政工队,为自己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由王博平乡长为中队长。党员林勃为指导员,政工队来的谢仁安、王忠孝为正副队长,党内组织支部为领导核心。中队(简称独中),我们政工队与部队一起行动,也是早上出操,晚上行军,放哨、军训,
与部队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行动一律军事化。除对部队进行文化、政治课以外,我们政工队主要在地方群众中进行深入浅出的抗日宣传及保家卫国等爱国主义教育,还作访问深入基层进行阶级教育,吸收贫苦群众和有觉悟的青年贫雇农参加部队,扩大武装力量。并对地方上不法分子进行教育惩办。所以我们部队所到之处,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称我们“独中”为“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的独中”。我们政工队在自己武装的部队里虽然生活紧张,但大家团结一致,精神上过得充实愉快。
因为我们部队纪律严明“为民除害”名声大振,我们部队所在地20余里外的地方,地痞流氓勾结原地方乡队伍之类,白天敲诈,晚上抢劫,弄得群众日夜不得安宁。一位从该地来我部队所在地药店坐堂的医生亲眼看到我们的部队所作行动,他就再三恳请我们部队到他乡为老百姓“除害”。通过队民和指导员同意,决定于重阳节前部队开往该乡,(事先保密)等到出发前,通知我和另一个女同志作向导,部队到岑外青峙执行任务。我听了既高兴又激动,因为部队能够流动到我母亲乡村,所以要我作向导。为使我不暴露身份把部队带到目的地,我就住宿到舅母家作掩护。
部队到达后,就立即按照原定计划目标执行任务,逮捕三名罪犯,二名地痞,一名原乡队员,就在街头原地枪决。那时已深夜十一时左右,我听到枪声后才告诉我舅母,她非常高兴,因她也受到三人之害后病更加重。第二天一早,家家户户都谈论夜间的枪声和看到我们连夜贴出的通知及罪状,都拍手称好。部队领导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告三人罪状,宣传我们抗日部队的宗旨,教育群众只有协助部队,保
家卫国,百姓才能过安定日子。为此,广大群众对我部队更加拥护,再三挽留我部队再留宿一夜。
第三天的拂晓,我在舅母家又听到枪声,我就立即起床预感到有不详情况。那天刚好是重阳节,舅母早就买好小菜,煮好粽子,我因情况不明,不能离开原地,以免失去联系。早饭后,一个满身泥浆我们政工队男同志向我处跑来告诉我,部队受到另一游击队偷袭,详细情况不明,部队除掩护还击外,大都向原炮台山撤离,我跑来告诉你。我见他满身是泥,就找出衣服给他换,要他爬上阁楼隐蔽,并带上粽子充饥,拿掉梯子藏起来。半小时后,又有一个政工队女同志急跑进来,我己知道情况,已有了准备,搭起木板,生了熨斗在桌上缝衣,就叫她一起坐到对面缝衣。一会儿一个男的嘴上不断地说:“我看见一个女的从大门进来。”他跑到我舅母家厨房,问我舅母有否见到一个女的跑进来。我舅母说:“没有见到。”他东张西望还是不相信,我舅母问他“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他说:“我们是来捉土匪的。”舅母说:“女人也会做土匪吗?”不等他回答,舅母又说:“土匪是坏,我家也吃过土匪苦头,你们辛苦了,早饭还未吃吗?我弄些点心给你吃。”随即把重阳节的小菜拿出来,这个坏蛋早已垂下三丈说:“我们半夜出来,肚子倒是饿了,吃些也好,有老酒吗?”舅母说:“我们做羹饭的老酒你先吃吧!”就立即烫酒,煮荷包蛋,弄得满厨房香喷喷的。外面传来“日本人来了!”这个家伙就立即出逃,我们二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又爬到阁楼隐藏起来,午饭后,听说日寇已回镇海县城,“土匪”见日寇来早就逃跑。村上屋里平静得一点响声也没有。我们三人就下楼吃过午饭,先叫男同志小周从一条小路出走,回到王贺乡队本部去,我与小顾二人过一小时从原路回部队。
当天晚上八时许,大部队和我们政工队员都到齐,就是不见林勃指导员,大家都急着说:“开始时指导员为掩护我们撤退,他站在路口,指挥着,后来就没有见到他。”越说心里越急,就决定明天一早到青峙原地去找,指导员的恋人余也萍,首先提出她去,我也立即提出我与她同去,因为我地方熟悉,又是我舅母家,就决定下来。领导嘱咐我们说:“刚战斗过的地方你们要细心谨慎,见机行事,尽量不要声张,暴露政治身份。”这一夜,我与也萍商谈,一直没有睡觉,我们作二手准备,一手准备死的后事,一手准备的活的打算,以家属身份出现,以免出另外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天未亮透,我们吃些点心,起步动身,一路上幻想很多,盼望他迎面而来,盼望他后面叫我们,特别走近小岙路上,盼望他从山上跑下来,种种幻想总成泡影。我们先到我舅母家,告诉舅母来寻找我们同志,坐下后,东边舅母、两边阿嫂、还有公公婆婆都走了过来,一边议论昨天的事,一边打听有否听到死人的事。一会儿对面的三公公背着扁担柴刀又要到山上去砍柴,看到我们在谈论昨天的事,他就说:“昨天早上八时多点光景,我在太平桥头对面山上砍柴时,只听到时高大的喊声,但听不清喊什么,又看到日本鬼子在延陵学校的一棵银杏树下行动,也看不清搞什么?”我们听了吃惊地说:“我们到这地方去看看。”因为这是我母校,四零年七月,日寇第一次登陆时,学校被烧毁,这棵庞大的银杏树依然存在,所以这地方就冷落起来,过路人也少了。我们二人直跑到这树下仔细观察,大树下有一滩隐隐的血迹,但见不到人体,我们在附近又东找西寻,找到离大树对面柴刺蓬里,见到一个尸体,面向下,背朝天,我们克制着悲痛的心情,把朝天的背反了过来,果然是林勃同志。我们二人泣不成声。面对悲痛怎么办?二人商量后仍回到舅母家,要舅母整理自家板,叫来可靠的熟悉木匠做棺材,一面拿了铅桶,热水瓶和昨夜也萍同志整理好的衣服用品等一起带到林勃同志地方,二人解开外衣,脱下也萍同志亲手编织的毛线背心和衬衫。见到胸部经过翻动以后还隐隐的流出鲜血。我们就将带来的棉花一个一个塞上,使他换上衬衫后再不染上鲜血。我们流尽了泪水,洗清了血迹,换上了衣服,数一数日寇的十七个刺刀口,我们愤怒和悲痛的心一起涌上,一定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木匠把做好的棺材抬到林勃同志处,他们帮助我二人一起安放好,也萍同志还在棺材边刻上姓名、年、月、日,以便以后找寻。因为当时的形势我们还是在隐蔽斗争的阶段。我们付好一切费用,感谢帮助我们的亲邻,就回到队本部。晚上,我伴着也萍同志一起,一边清洗血染的衣服和毛背心,一边回忆我们与林勃同志在一起的情景。她说,她认识林勃同志是在四零年下半年,在镇海蟹浦流动施教团工作时,我认识林勃同志是在随军服务团,他还是我们党小组长,他离开时说到别处去,不能说去向,这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我们第二次相见多么高兴!谁知在一起战斗只有二个月却成了永别。她说:“革命,要有牺牲,胜利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安慰她,她却教育了我,我们边说边洗,不知不觉到了东方已白,小小的河池,染红了烈士的鲜血,她把洗好的毛背心晒干后,在常青色的毛背心上,用红色的毛线在十,匕个刀口上绣上十七朵红花,作为纪念。她经过北撤南下,在紧张激烈的三年战斗中一直珍藏着直到全国解放。可谓革命的爱情之浓厚深切!
“独中”受到打击后,国民党顽固派,也加强对我党威胁,上级党决定我们“独中”与三北我党“三·五”支队合并。部队和政工队员一起撤离到四明山地区,我因工作需要被留下仍坚持原地战斗。组织上要我找一个比较隐蔽、交通义方便的地方安下身来,建立一个联系点。我通过亲友介绍在长山桥附近方沿林新建的一个保国民小学教书,但待遇很低,每月只有一袋稻谷。我见该校地方靠山,走出数步,又能通大路,交通很方便,是我们理想的场所,就答应下来。离学校开学将近数天,又有一所长山保国民小学聘请好的教师为了待遇太低不来了,我知道情况后就与同学李雅琴、唐惠珠二人商量,我们三人把这二所学校一起包下来。每月二袋稻谷我们三人共同吃,生活也可以维持了。而且二校相距较近。只隔一路一桥,约一里多路。就这样,我任方沿小学校长,唐为氏山小学校长,李为二校的任课老师。
开学前几天,我们就到方沿小学校董处,该校校董是个老农民,非常朴实,见到老师也很尊敬。他说:“我们是一所新办学校,为了小学生过河过桥过路不方便,所以我们在自己的村上办所学校。老师是辛苦的,每月只有一袋谷,这是政府规定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对他说:“这倒没有什么,我们也是为了人民教育,现在和你们商量,就是我们有二个女教师,一个是长山小学的老师想住在你们村上,请你校董帮我们租一间宿舍。”他听了很高兴,爱:“老师住在
我们村上很好,我一定想办法。”第二天,校董就给我们租到时一间房子,连吃饭也在这户人家。特别是这户当女当家很客气,说:“女老师吃得少,蔬菜我们自己种,鸡蛋我们自己鸡生。”
开学后,我们三人,二所学校,每校只设二个班级,每班都是复式班,轮流教育。特别是李老师,又到方沿又到长山,担任音乐、美术和体育,总是忙忙碌碌。我们二个校长,每校二班级,也是教三、四年级,又教一、二年级,每天上课不停,弄得喉咙也哑了。晚饭后还到学生家访问,熟悉了解当地情况。晚上我们一起学习《大众哲学>、《论持久战》、《论新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政治书籍,也学习《新青年》、《民主、决定》等进步刊物,三人生活过得又紧张又有规律,学校也办得很有生气。到我们学校来的同志都赞扬我们,当地农民群众也很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学校,我们能听到自己孩子的读书声、唱歌声,孩子也活泼了,懂道理了。”在植树节那天我们与家氏、校董等在学校周围还种了许多树木和好看的花卉,家长们都说:“我们老师没有架子,和和气气与我们如同一家。”都希望我们把他们的孩子教到毕业。
一学期快要结束时,我单线联系的党领导(邢老师)到我们校来。问我们下学期怎样打算。我们说:“校董,家长都要我们留下继续在这学校。”雅琴急着说:“邢老师,你有办法到更有趣的地方去?”邢老师笑着说:“有趣的地方,但是更艰苦更危险呀!”雅琴即说:“我一定要去。”邢老师 走时对我说:“你要对雅琴、惠珠做好教育工作,特别是雅琴。”同时,也要我作好离开这个学校的准备。邢老师走后,我们议论着去向。我说:“去三北和四明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可是雅琴是独养女儿,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她说“我不管,你们去,我也去。”惠珠说:“我没有问题,母亲有大嫂照顾。”我说:“我们即便去,也要做好家里的工作,使以后也不要有什么影响。”惠珠说:“我仍早说到别的地方教书去。”雅琴拍着手说:“我也可以这样说,这次跟你们教书来,,妈妈不是也很高兴吗?”我说:“这次你爸妈都知道这个地方,将来去的地方可不能告诉了,你爸妈问起我来,我也无法回答呀!”雅琴坚定地说:“反正我不会暴露你们一切,家里工作我想办法做好。”我早知道雅琴要到游击区去,我本想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后再送去,现在她决定要去,先送她去。第二次邢老师再来我校时就决定雅琴、惠珠由他带领进山去。我另调一个学校,仍坚持在秘密地区工作。其实我也多么想到游击区去,可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要服从组 织的决定,就愉快的接受了新的任务。
四二年九月,学校又开学了,我按照党的指示去横河公德中心小学任教。该校是一所原为私立改为公立中心学校。原私立学校,是一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大本营,该校校董几个儿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有去过陕北共产党教育的党员,为此以该校为中心,把全乡的学校都搞成抗日救亡的阵地。组织抗日宣传队、剧团、歌咏队,还救济贫民,协助农民播种子,还组织抗日锄奸等工作。把该乡抗日运动搞得热气腾腾,把陕北共产党抗日的一套搬到该乡来实施,成了红色的堡垒。但在全国形势起着变化时,国民党顽同派又积极反共,影响该乡该校的工作方法转变,把面目搞红了的党员撤离到别处,把私立改为公立,由县政府接办,校长、教导等教师大多更换,可是我党建起来的基础和基层群众仍然要巩固坚持。党就派我到该校去,一面积极与校长教师等作好团结教育工作,一面和地方上积极分子和党员保持密切关系,作好保护教育,改变工作方式。并安排地方上的党员、积极分子隐蔽,使工作稳步地进行。我在该校任三、四年级班主任,星期天不回家,我只说家里无人,母亲在上海亲戚家,平时借口到学生家和附近群众家串门,除学校工作外,也不搞出头露面的工作。学饺的事,不管份内份外都帮着做,所以校长和教师对我都很好。有一次,一个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对我们校长说:“你们校里韵一个教师经常不同家,听说是原来李校董的亲戚,很值得我们怀疑,你要提防她。”这位女校长是一个国民党党员,由于我们关系还好,也比较能说公道话,也热爱教育事业,于是就说:“这教师是教育科派来的,和李校董根本不认识,怎么是亲戚。你不要乱说我教师,我校长也难当呀!”后来校长对我说了这些话,我笑笑说:“到这学校来做教师不回家也要怀疑吗?”教师们也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按过去的事来看,就是李校董的亲戚难道都是共产党员吗?”幸而校长与教师对我信任。我安全稳妥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四三年七月学期将要结束,党的领导告诉我学校结束后马上去四明山党校学习,我听了高兴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回想入党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觉得自己在对敌斗争、对社会上的事物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有了提高和认识,但在党的系统理论上知之甚少,渴望学习的要求在我脑子里越来越迫切。
七月二日,我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四明山“中共浙东区党委”所在地梁弄党校报到,见到已有好几个同志先到。一会儿有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女同志跑过来叫我,我听后呆了,因为我是秘密地区的不能用原来的姓名,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在“独中”时的小方,原来她四一年随部队到三北后就来司令部政工队,她比多小,这次也来党校学习,我们又在一起高兴得很。
七月三号,党校正式开学了,谭启龙政委,宣传队长张瑞昌(顾得德欢),党校主任谢飞(曾是刘少奇夫人),指导员巴依云二个都是女的,其他也都穿灰色军装.学员中穿军装的也有半数。听说这一期除在部队以外,还从各地方党委区一级干部中调来培训,共分四个班,我与三北各县来的编在一起。生活都是军事化,除几次军事演习外,都在梁弄镇上集中一起学习。
学习内容:四个方面:一、党的建设,二、统一战线,三、游击战争,四、民运工作。以上讲课都是党委领导和部长来讲的,有理论又有实际工作例子,深入浅出,使我们学习后有很火的收获。如对党的认识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提高,对统战工作义团结又斗争,通过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运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民运工作方面杨思一同志讲得更为生动实际,对我们秘密地区工作更有适朋。在游击战争方面,因讲话不。障,自己又实践体会不够, 所以印象不很深。
原定学习三个月,因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派,集中各方部队要向我们四明山区进攻,我们部队也要进行战斗准备,区党委决定,提前结束,我们的学习班就在九月底结束。
我回到镇海向党领导汇报学习情况时,领导告诉我,我们地下武装第五大队在撤离中牺牲指导员和副大队长二位同志,部队已撤到四明山,我们也要离开到宁波敌占区去,要我回到家里,简单告诉母亲说:“我又要调学校了,这个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好读书对我将来工作有很大帮助。可只吃饭,没有工资,请母亲原谅。”她说:“工资倒没有关系,你原来学校里发来的稻谷我都存在阿姨的媳妇处。就是你在什么地方来信告诉我,我是多么想念你,别人问我,我也讲不出。”我对母亲说:“你应该相信你的女儿,我们家过去来的一些朋友你也知道,你不是说他们都是好人,都是为贫苦人做事的好人。你不识字,我来信留下地址,不是要找来麻烦吗?我有时间一定会来看你的。”母亲低低头,表示也理解我。
第三天,我与三东地委领导和他的妻子及刚满六个月的儿子一起到达宁波敌占区。我改名小妹,说是他妻子的表妹,是来抱小孩子的亲戚。我称呼他们二哥二姐,先到一个地下党员家,他家无人,有二间房子,厨房等都齐全。听说他家母亲到乡下四哥家去了。三嫂到上海娘家去了,该党员吃住在店里,有时到家里看看就走。
一个月后,他母亲和嫂子要回来了,我们又搬到城外西门一个党员家。这家只有一个母亲,房子很小。有一个好处这个母亲能照顾我们的小孩子,吃饭等也可以托她代办些事,身体也好。可有一个问题,到城里来进行工作,必须经过两门卡口日本鬼子岗哨,行礼、查问,早上、晚上日寇铁丝网就关上,碰到什么情况就不能通行了,觉得很不方便,又托人找到地区中心地城隍庙边象鼻巷,房东只有一个老太,儿子都在上海外地。房子较好,她靠房租收入,租价较贵,我们为了只有一个老太,房租贵些也就住了进去,可是这个老太是个精明人,又爱管闲事,很健谈,我们的进去来往客人都要过问。有一天,问我说:“你姐夫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是舟山到宁波做渔业生意的。”她就在我姐夫来时,问这问那,问渔业生意等等。有时领导回答有困难时,我与二姐就过来解围。弄得我们也很伤脑筋。后来,我们索性想个办法,学会打牌,客人来了,就拿出麻将牌来作掩护,平时,我们要做些工作,也靠假打牌来掩护,总算摆脱房东老太的麻烦。
四三年十月后,国民党顽固派用超过我十倍的武装进攻我四明山地区,我们动员全民进行“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形势很是严重。敌占区日寇也趁机配合国民党到四明山不断进行扫荡,在宁波城区,汉奸之流对我地下党也加紧搜查、逮捕。
四二年底,我党在城区另一个二东特派员突遭逮捕,我们就通知城IX所有秘密党员了解被捕情况,经过多方设法工作,被捕原冈纯属敲诈性质,毫无证据和口供。关押半个月后通过种种关系,损失一些金条,交保释放。出来后,经上级领导决定,把三东领导机关全部撤离到我三北游击区根据地,领导的妻子、小孩子都到上海亲戚家去.我与三东付特派员和另一个女同志丁菲也到三:I匕,我们与毒药火队同一机关,分往二地,他们与海防大队长张大鹏,政委吕炳奎,吕
妻胡英及儿子等。我们是付特派员王起,我和丁菲,另有一个通讯员,我们住在镇北田央王,他们住在慈北海岸边,相距不远。 t
那时,我为三东地区(鄞东南、镇东南、奉东)政治交通,丁菲为机关负责,都属王起同志直接领导。我经常跑宁波城区邓东南县特派员楼君归处(即吴田)又跑镇海江南县特派员陈志达(后为罗德生),只接上几次关系他就调别处。在去镇海时,我到母亲处,告诉她我已在四明山部队工作,要她放心。因为母亲知道一些我部队情况,只说你自己小心好了,有事我会到舅父家去的。奉化县特派员张国璋联系过儿次,因奉化划归到另一系统后就未去了。
四四年以后,四明山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全国形势也起了很大变化,为了加强城市工作,浙东区党委决定,由区党委直属领导下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由于文祥为书记(原敌工部长),粟后为副书记,王起、王槐秋为委员,我们的机关就从三北搬到四明山“梅岑”城部所在地。王起仍负责三东秘密地区工作,我为城工部的政治交通,仍由王起负责领导。以跑宁波敌占区为主,直接与邓东
南县特派员楼君归联系。主要传递区党委的指示,并要求搜集敌、伪、顽的动态,敌占区各行各业各种团体的情况和各阶层等群众的反映,包括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和思想的各种动态和言论以及军事、经济等等。使区党委能及时了解分析,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以便领导正确作出针对性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我的工作在组织上有紧急任务时,就立即行动,一般情况可以隔几天去跑一次,我常是以步行为主,因为步行可以随机应变,乘船等也以小船和航船为主和基层群众一起。因为那时汽车、轮船上都有特务、汉奸和伪军等。步行虽然也要经过敌人岗哨,看到岗哨查得紧时,可以缓行或绕道从另一路走,有时和群众一起走不使敌人单独注目,碰上紧急任务,要立即行动时要准备好必需掩护和牺牲品之类东西,并要准备好几套口供和附合打扮自己身份所带物品。如在三北是棉花产地,要了解熟悉棉花等情况,说起来合情合理,如带香烟要了解香烟的种类和行情。一路上要熟悉这条路的情况,路远时要在中途熟悉几户基层群众交好朋友,以便必要时可以作隐蔽歇脚之用。有一次,我从城工部到宁波,走到大隐地方,远远望去见日寇大片人马向大隐这条路走来,我就立即走另一条小路,弯向小村庄走进一户农家,避过日寇的视线,就安全渡过了。
四五年上半年,全国形势有很大的好转,我们四明山经过第二次反顽战斗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的敌后游击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各方面的行政组织更加健全,在梁弄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政权工作更加强,武装部队更扩大。敌占区的调查也有进一步要求,所以我来宁波的时间和次数更多了,为此我又建立了几个立足联系点。一个在小梁街19号,主人原是我随军服务队的女同事,回家后服侍母病,没有工作,她的弟弟是一个地下党员在外工作,别无他人,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第二个联系点在开明街户口丝巷一号,唐采英阿姨家,阿姨是一个孤孀,无子女唐因病,住在她家,唐又是我在公德学校时的支部成员,我就在这二家点上轮流往返住宿,在敌占区工作得到她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每次把各方面的资料送到城工部,大部受到城工部领导的好评。“宁波城区的资料,较为全面细致,很有条理,参考价值较大。”
鄞东南县特派员楼君归(即吴田)在敌占区为什么能搜集到这些较为全面的资料呢?因为他有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堂兄楼耀卿是楼茂记酱油店的总经理。他原是邓东南县委委员,在农村学校以教书为掩护,负责党的地下工作,四二年二月,上级领导决定,根据形势需要,要加强敌占区工作,因他有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个堂兄,在宁波城区江东楼茂记任助理帐房。这个堂兄弟总经理识字不 多,但做生意经验极为丰富,又有一个大胆泼辣的性格,自他任总经理以来,楼茂记酱油店生意兴隆,是宁波城乡酱业的大户,有分店四、五家,在商界中有很大的威望和信誉。所以在成立全城的酱业公会时,一致推选楼耀卿为酱业公会会长。该位堂兄对这位堂弟也很器重和信任,认为在楼家族中,在宁波城区是数一无二的高材生,有学识,又有政治头脑,做事认真、品德高尚,是他理想中的助手。他当选酱业
公会会长后,就聘请他担任亲信秘书。他经常夸耀说:“我有丰富的生意经验,你有高见的政治头脑,我们一定要把楼茂记的酱业搞得兴旺发达,成为全城“独秀”。”我们党就利用这个条件按插秘密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该总店分店,做练习生和职员等,为我党的力量(因为日寇占城市后,大多数党员都撤退到农村)也通过这些条件输送农村进步青年到四明山根据地参军,特别是以酱业公会秘书身份对各方面联系,接触各阶层人士和要求进步青年,广交朋友和中老年会员,依靠楼耀卿的威望,取得了他们的好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又利用楼茂记的经济优势,慷慨支援基层群众,为我党发展基层力量打下基础。总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时时处处为党扩大力量,完成党的任务。我每次到他家去,他总是忙着通宵整理材料。缮写稿件,基本上用两种方法:一种用明凡水写在包装纸上,包上物件到城工部后用碘酒一擦,每个字就显出来;另一种是用极薄的软纸,写成小小字,卷成细绳,缝在衣角,衣缝中或藏在长发中隐藏起来,来不及时我与他一起整理抄写也常到通宵。晚上煤油灯光照射,就用黑色纸或布包围起来,进行工作,总弄得筋疲力尽,但听到领导说,资料价值有用时,心里才得到安慰。
四五年六月底,城工部突然接到一密电说:“宁波城区日寇宪兵队要逮捕中共在宁波活动的领导分子。”城工部领导当夜告诉我,要我立即一早乘轮船到宁波要他化装立即进山来城工部。我一夜未睡好,计划怎样进行。第二天到宁波后,急到楼家他家“五弟(即楼君归)刚在家。”三嫂告诉我,母亲到四哥家去,要我多住几天,我说:“今天有急事,下次再来。”说完告诉五弟情况,说领导要他立即进山去,
他也急了,说一点没有准备,怎办?我说:“我早己想好,说我母亲急病要到外地治疗,因我是独女要他陪同一起去,告诉三嫂与耀卿哥说声,我们就立即动身往西门外从鄞西横街头进山,这条路虽然远一些,考虑比较安全,万一遇上什么问题,还可以到横街头四哥家作掩护。”他说:“你想得周到,就这样。”我们进到山区,才放下了心,五弟说:“山区的空气真舒畅,在宁波紧张的气氛真是使人透不过气。总想到自己的游击区来工作,但为了党的需要,只好服从。”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到下午四时才到城工部(又称大陆商场)梅岭目的地。
秘密地区来的领导,有一间密室,吃饭等都是通讯员送的,不与山区的同志见面交谈。我把客人交给领导后,就准备吃饭去了。领导立即叫住我说:“这位客人你还是要负责任的,明天我给你任务。”第二天,部领导来我处,给了纸和书笔等,要我负责联系,要他在这里多看些书和文件,同时写些材料,总结一下工作,要他不要太紧张,在秘密地区工作的同志这些文件和书刊是很难看到的,今天因我们有
会议,等明天会来看他。
“七·一”党的生日,我们都去开会,他虽没有参加庆祝大会,可中午增加一碗晕菜他也享受到的,不比在敌占区“七一”还要受到敌人的警戒呢!通讯员还送来当天的新浙东报。他很高兴地说:“我入党以来第一次这样愉快。”
一个多月过去了,四五年八月十三号夜里,由浙东区党委来电,告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我们兴奋得全夜未睡,城工部领导也连夜找五弟谈话,要他立即动身去宁波,准备接收日本投降事项。十四号早上,我拿了新浙东报号外,送到五弟处,他己动身到宁波去了。
几天后,我跟城工队领导王起同志来到宁波五弟家,他汇报,城区日寇动态仍然如常,又汇报了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城区工人和基层群众情绪极为高涨,潜伏在电话公司的党员电力公司的基层工人也已有新准备。多数市民还是猜疑;上层人士互相暗告;汉奸之流不安情绪较严重;日寇内部消极厌战严重;但外表仍很镇定。城工部领导了解情况后义进山研究,过了几天,调来在慈溪秘密系统的负责人周明(即周明)及他领导下的胡章生等骨干来加强党的城区力量。积极步骤,城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环卫工人、原有的抗日反攻同盟等队员约二百余人组织武装到庄市我游击区准备训练,接管日寇投降时,配合四明山武装队里应外合的战斗。
五弟由于日以继夜地工作,劳累过度,突然病倒,鼻孔出血不止,急救到美华医院(现第二医院)住院半月后出院在家休养时,正是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九月下旬城工部原领导三东地区负责人王起同志来宁波城区告诉我们说:“毛主席与蒋介石在重庆会谈已结束。我党为了顾全人局,我们在民江以南的抗日根据地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北,所以我们在宁波对日寇接受也不进行了。”我自八月下旬穿着一件凡士林布旗袍来宁波后,一直协助宁波领导做接受日寇的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再进山。现在我们党、政、军全部撤离四明山,我也没有必要去拿衣服了。
在宁波眼看国民党军队和接管人员大批进城,我们一面了解国民党的情况;一面准备坚持下来的打算。首先是做好基层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明党的方针政策,特别对动员参加武装的基层领导讲明道理,并对准备参加武装人员解决生困难,安定情绪,做好党的保密工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问题,其次千方百计寻找安置坚持下来同志的职业和生活等。坚持下来的同志做到社会化、职业化,更重要的是职业化,有了职业才有立足之地。于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逐步解决了职业。如原三东地区负责人王起与地下党员开设一家新新服装公司,作为股东之一为掩护。如原五弟(即楼君归)通过堂兄楼耀卿总经理对他的信任,利用楼茂记酱油店的资金和楼家祠堂的地方,以公益事业为理由,创办私立“和平小学”,楼茂记酱油店的楼耀卿为校董,楼君归为校长。并为当地贫苦子弟免费和半免费。学校办起来了,校长有权聘请教师,五弟就把农村任教的党员骨干和原好友中的进步同学和进步教师都聘请到学校任教。一学期后,由于教育成绩好,又有免费利半免费的学生,原有的六个教室就不够用,就又和楼茂记的这个堂兄商量再扩建六个教室,就成为有六百多名学生的较大的私立学校。既安排了地下党员的工作又成了“宁工委”的联络点,成为宁波地下党的指挥中心。慈溪秘密系统负责领导周益明同志与胡章生同志,开设小型织布厂。除自己为老板以外,还能安排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骨干等,为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再把原邮电部门的党